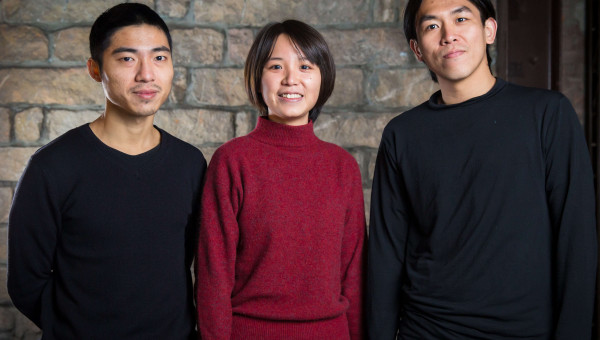「生命很殘酷也很沉重,因此想更輕盈的去看待。」——專訪《告別進行式》導演吳文睿

導演吳文睿,2011年以南藝大紀錄所畢製作品《當我不存在就好》在「新北市機不可失主題紀錄片影展」嶄露頭角,睽違七年的創作《告別進行式》,也入選了第11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導演紀錄了家族裡愛拍照的叔公,並以叔公的告別式影片出發,透過幽默有趣的角度闡述叔公面對生命的豁達,帶領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生死。
以下為與導演吳文睿的訪談紀要:
這次會入圍我也很意外,因為已經很多年沒有創作了,從南藝畢業之後到去年《告別進行式》出來好像過七年了吧! 我個人的創作其實不多,但都是拍「人」比較多。
紀錄片要去處理人的「技術問題」非常複雜
我在拍《告別進行式》時,也有想過要試著不要以人為主,讓它是以一個概念或議題為主的片子。但有的時候不是你想拍就可以拍到的,特別是脫離學生的身分之後,沒有辦法很任性的說我想拍什麼題目就去拍,可能會有經費的問題等等。不過,因為有一些朋友覺得我蠻會處理「人」,可以把人呈現得比較鮮明、立體,所以後來也是有一點半認命,覺得叔公這個題目剛好碰到,那就再以同樣手法試試看。
我覺得紀錄片要去處理人的「技術問題」非常複雜。不管你跟這個人有多熟,即便是認識非常久的朋友,可是當有一台攝影機擺在你們中間,你們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就是從零開始去累積的。這個關係會牽涉到很多問題,例如:你該不該拍、 你該不該問、你什麼時候該拍什麼時候不該拍、什麼時候要帶機器什麼時候不要,什麼時候要問問題什麼時候不問,這只是拍攝的階段,而同樣的問題在剪接的階段又會再問自己一次。
十幾分鐘的片子做起來比長片還要痛苦
《告別進行式》的製作過程其實非常痛苦。第一個部分是,老人家很難拍啊,特別是很難訪問。以叔公為例,比如說我想知道為什麼他要拍這麼多照片?其實我大概有猜到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可是他給你的回答就不是他真正的想法。而且叔公真的滿強勢的,本來想說這部片可以做得更有後設意味,像是放入我是怎麼做這支片子的,從這邊去反映出影片性格,我的上一部片子就是這樣做,但這部個片子這樣又走不通。所以在剪接時,有時候會把紀錄片當劇情片在剪,但同時又不能讓被攝者覺得,這個故事是我編出來的,要想辦法走到那個現場裡去。
政大的郭力昕老師曾經在評論中提到,他認為所謂的「家庭相本」是很不真實的,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只會拍下快樂的時光,不會拍到生命中那些比較陰暗、傷心、或是在爭執的場景,甚至根本不會拍到死亡,他認為拍這些東西會把它昇華成一個作品,好像這樣的事是攝影家在做的。我覺得這個看法有點太菁英,因為像我叔公就是一個特別的例外,他就是從年輕到老一直在拍這些東西,像是他小孩走了、他太太走了,躺在棺材裡面,他也都會拍下來,但就像片中講的,他覺得這個沒什麼。
不過,這也牽扯到影片裡另一層技術的問題——叔公拍的照片該怎麼放?他的照片該怎麼呈現?這個東西我想了非常久,因為當我把照片這樣一張一張播放的時候,那是沒辦法看的,當靜照變成影片的時候會牽扯到美感的問題,我會覺得那個東西很粗糙。為了解決這問題我也花了蠻多時間去想,最後是想到,我們在看家庭相本、小時候的照片、爸媽的舊照片時,並不會一張一張非常專注的看,而是攤開相本一頁一頁看的,我們看的是氣氛以及當時的情緒。
另外,雖然不做創作很久了,但我還是在拍片,在接案子。大部分案子都希望攝影拍得漂漂亮亮、聲音收得好好的、主題明確清楚,甚至要比較光明正面,主旨清晰,時間又很短,因為多花時間可能就多花費用,所以必須把可控制的因素儘量去拉好。因為我也很久沒有自己拿攝影機拍東西了,所以當我再回來拍這個片子時,想試試看用很低線的方式,用很簡單的機器做到一定的品質,但有時候還是會回到那種拍案子的慣性,比如說,如果是案子,攝影機可能各種大小各種角度都有,可是有時候去想,真的需要嗎?可能只是怕剪接的時候素材不夠而已。加上我覺得每個東西都是高度的濃縮,在決定每個鏡頭的長度、內容時,裡面每個物件或訊息都可以去折射出更多層意義出來,難度不會比做長片還要容易。
以唐吉軻德式的樂觀抵抗孤獨
我覺得叔公是個矛盾的人,他真的不怕死嗎?拍攝的那一年多也是他身心最不好的時候,他長了骨刺,在猶豫要不要去開刀,擔心自己年紀這麼大如果開刀身體會不會就廢了,我覺得他其實也滿怕死的,雖然他在做的這些事情讓大家覺得他對於死亡看得相當豁達,可是一有小毛病他還會很緊張。
他想用這個片子來完美他的人生,不會提缺點,只會提這個人人生中好的事情。我拍了這部片後才發現,很多老人其實都很怕被忘記,就像之前的電影《可可夜總會》以及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也寫過類似的東西。因為害怕接近另一種死亡,怕沒有人記得他。他揮舞手上可堪運用的紀錄工具,透過各式各樣的努力去抵抗被忘記這件事,我覺得有一點像唐吉軻德。而且他兒子沒結婚,所以也沒有孫子,以後可能也沒有人祭拜,到了我們這一輩,甚至下一代,有沒有人記得他都不一定。
人生的情緒有時候是一體兩面,一個是光,一個是暗,難道你要一直沉在暗裡面嗎?如果說必須要倚靠一邊才能往前走,那我覺得至少他願意去面對,因為孤獨,所以必須要樂觀。
以幽默敘事手法處理悲傷之輕
這部片當初是丟觀點短片的徵件,所以一開始就是以短片去發展。同時這個素材的厚度其實還不足以去發展成長片,但是我試圖想要在一個短短的篇幅內達到敘事的企圖,希望不只是講一個概念,而是可以真的有一些敘事上的情緒起伏、有一些懸念。我不喜歡把一個片子處理的太悲傷,悲傷的東西偶爾也要用比較輕一點的方式去處理它,在感受到那個輕的同時,也會覺得「那個輕有一個重的東西懸在下面」。所以我覺得創作的時候幽默感很重要,即使是比較悲傷的片子,幽默可以讓我們比較輕盈地去看待。
我當時也花滿多時間去思考音樂的,因為我不喜歡紀錄片的音樂是一種襯樂、只是一種襯在下面的情緒。大部分的樂器不是鋼琴就是木吉他,或是後來流行用一些噪音,可是我想要的是一個敘事性很強的東西,因為影片與音樂是對話關係,所以我覺得必須做到如果把音樂抽離,那一個片段就不成立。
我自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當觀眾,所以「幫觀眾想」對我來說很重要,他們願意花時間來看我的作品,我就必須讓他們產生某種共鳴或對話。我覺得某些東西會超過真實的層面,而我只是在用我這些素材講一個我想講的故事,就像我這個題材要再更接近真實,但有些沒有辦法放的素材反而會讓我們覺得更撞擊,可是這個真實到底是傷害性的真實,還是說是你以為的那個真實?所以要講一個可以跟觀眾溝通,讓觀眾願意看下去,讓他們可以有一點共鳴的故事,不然就會掉進作者個人的情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