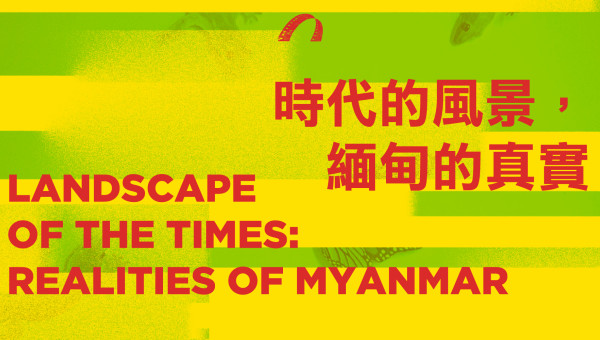在記錄中玩轉虛實: 專訪《卡努托之傳說演繹》導演厄內思托.德卡瓦留 Ernesto DE CARVALHO
日期:2024年5月15日
地點:京站威秀影城
採訪撰稿:許惟珊

兩位導演如何認識並展開合作?籌備和拍攝期間又是如何分工的呢?
我和 Ariel 是在2007年認識的,他是我在當地部落的第一個學生,我也是他第一個電影老師。後來我們慢慢成為朋友、夥伴,已經合作非常久,這部作品也花了大概10年才完成。
因為密切合作了很久,我們之間其實已經很難明確區分彼此的分工。不過任何雙人組合作都存在互補關係,比如 Ariel 是當地原住民,可以很自然的與當地人互動,在鏡頭前的效果就會非常好,因此他比較著重現場的氣氛,試圖塑造出可以拍攝到我們想要畫面的氣氛;而我通常主要思考影片的架構,考量在設定好的架構下,需要什麼樣的畫面、內容,才能合理支撐起故事。
片中有時有劇本安排,有時又讓演員自由發揮,想問導演主要以什麼方式指導演員,又與他們保持什麼距離、關係呢?
舉例來說,卡努托祖母在跟他講話的畫面,我們是現場直接請演員想像,在這樣情境下,祖母會跟卡努托說什麼,她就想了一下直接說出來;所以各位聽到的臺詞其實不是死記硬背的臺詞,是她自己發自內心說出的話,所以會比較真實。
另外,其實現場攝影師、燈光師等拍攝團隊成員都會隨時提出意見,這是一個很開放的環境,大家都能自由發言,共同塑造出適合的場景。 例如卡努托的葬禮之後,妻子獨白那段其實本來沒有拍,是過兩年後才補拍的。當時是攝影師提出意見,認為妻子應該要出現在畫面中,我們才又邀她來補拍。當時也是請她想像:在這樣的情境中,妳的角色會說什麼?結果那位演員後來回家整晚都沒睡,都在思考要講什麼,到了現場連拍3次,她就連哭3次,所有臺詞都是真心誠意講出來的。在大家都能真誠表達的環境裡,就會得到非常好的拍攝效果。
當初如何決定要採用與當地人共同創作的形式呈現?您參與部落影像工作坊(Vídeo nas Aldeias)、製作多部原住民電影的經驗,如何助你形塑出自己的導演風格?
邀請被攝者參與、合作的拍攝方式,是我一直以來的興趣。我對電影形式很感興趣,因為常常就是形式上的一個小小的選擇,會大大影響後面的拍攝發展跟結果。
我認為教導別人就是最好的學習方式,常在教學過程中學到很多新事物。提到導演風格,或許大家對於導演的想像可能是比較西方式的——負責指導、指揮演員與工作人員該做什麼;但我會想像拍電影的過程像一種遊戲,而攝影機的存在是為了要去觸發某種真實——攝影機出現,便能觸發真實的反應或者現象——將這些反應記錄下來,也許就會自然而然地帶領我們往某個方向前進。

片中大量混剪虛構和真實的影像,更常常以揭露後台的方式讓觀眾看見拍片以及「說故事」的過程,導演如何看待真實和虛構之間的關係?當地居民又是怎麼想的?
這部電影就是要讓觀眾看拍電影的過程,劇情跟紀錄之間的界線非常模糊,有些看起來像是純粹紀錄,實際上是重演或是演出,但我認為那些部分也許反而更趨近真實。
其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怪罪,或歸功於這些演員,我們一開始有點希望大家不要演太好,這樣觀眾比較容易看出哪段是演的、哪段是真實情況;但他們的演技很好,以至於後來變得虛實難辨。到了後期剪輯階段,我們就決定放棄引導觀眾分辨真實和虛構,決定讓它如各位所見。
而當地居民後來也對這樣複雜的形式感到好奇,甚至是喜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拍出來的故事就是卡努托傳說的某一個版本,不是官方權威、企圖要統一大家的想法,因此並不會抹殺其他人對於這個故事的想像,也保留了不同詮釋的空間。
卡努托的傳說故事在當地帶有負面意象,團隊最初如何邀請村民加入?又是如何與村民共同討論拍攝畫面和敘事?
我們也了解卡努托的故事在當地算是禁忌話題,很多人不願觸碰。後來經過思考,想出「電影中的電影」的形式,邀請當地社區加入一起想像如何建構這個故事。當然一開始有些人的確比較遲疑保守,不太想談論,但後來他們發現可以透過說故事討論很多當地議題,便非常希望以當地人的視角說故事、反映在地觀點。
這整部電影對我們來說也像是個巨大的說故事遊戲,當地本來就有在聚會中說故事的傳統,日常生活就會不停接觸到許多不同的故事,對於參與徵選飾演卡努托的小朋友而言,說故事的經驗、傳統就因此和拍電影的過程結合在一起。
討論拍攝畫面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語言,我雖然聽得懂、也會說一些當地語言,可是有些概念非常複雜,還是需要有人從旁協助翻譯,才能剪輯素材。這也是個不斷調整、非常彈性的過程。
我們的工作坊除了扶植原住民創作者,也在當地辦剪輯工作坊,致力培養原住民族剪輯師,因為剪輯其實是最困難的,一般習慣使用電腦的人學剪輯很快,但對於不熟悉電腦操作的人來說,剪輯門檻就很高,需要花更多時間學習。其實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電影都有一樣問題——有人拍電影,但會剪輯的人相對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