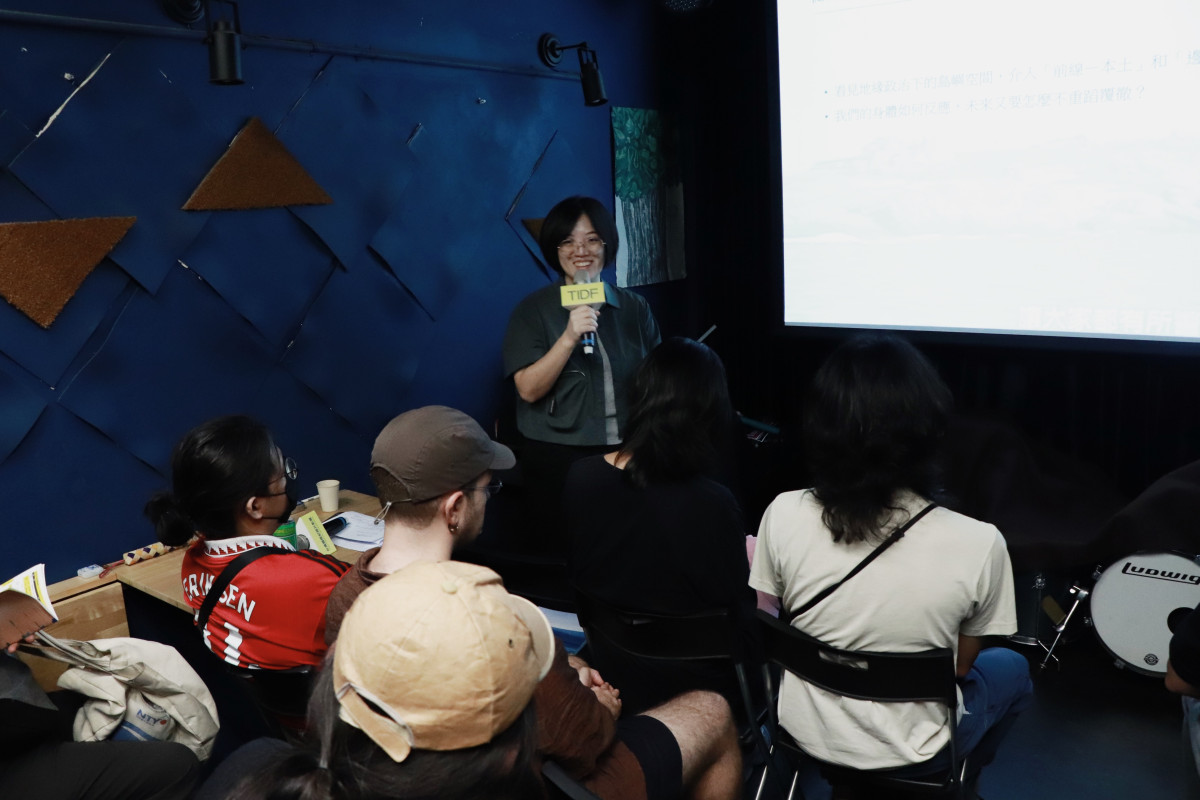邊界決定身份?「流離島影」的國族與島嶼意識|主題講座
時間:2025.06.27(FRI)19:00
地點:江山藝改所
主持人:趙元
出席講者:趙正媛
攝影:翁皓怡

主持人
今天很開心請到趙正媛來跟大家分享,那正媛以前做過就是「流離島影」的相關研究,然後他去年也受《Fa電影欣賞》雜誌之邀,就是有採訪了「流離島影」系列的總策劃周美玲導演。他對於這系列的影片非常熟悉,那等一下的分享,最後也會留一點時間給大家發問,或是大家對於作品有任何想法,都可以那時候交流,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正媛。
趙正媛
嗨,大家好,我是趙正媛,那我平常就是做電影文字相關的工作,我就是寫了一些影評,然後採訪了一些影人,對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包含明天還有一場在赤子的研究都是跟「流離島影」這個主題有關的,那因為這些都是我,大概六、七年前,然後到現在陸陸續續去研究出來的東西,但是因為這都有一點歷史了,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可能看過我以前發表的東西,那我今天會稍微做一點修正,對有一些我當時沒有搞清楚的東西,那我覺得也會直接影響到我怎麼去分析紀錄片。那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我就坐下來談,我的講稿在這(笑),跟大家娓娓道來。
首先就是這一次的題目:「邊界決定身份?」那其實如果是地理系專業,或者是比較做「邊界」研究相關的人,那他們其實一看到就會大概知道我想要講的範疇是什麼,所以我今天主要的話,就是放在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怎麼從比較政治脈絡或是社會脈絡去理解「流離島影」的重要性;至於明天的話,它會比較從台灣紀錄片的美學,或者是歷史,以及製作方式的這些轉變來看,所以這兩場講座內容會比較不一樣,那我今天就以這個題目為開端,我想要先談的是:這個邊界會怎麼去影響我們解釋這部紀錄片?
那首先,我想要先簡單定義一下我所謂的邊界是什麼。那我們一開始想到邊界可能會直接想到的是地圖上固定的那種實體線,好像國與國之間是可以很明確的,用一條線去區分,但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嘛,我們實體的空間都是在現實世界裡面,佔有空間,而且具有一定的質量,然後也會有活生生的人,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在這樣子的一個特定的領域去進行的活動,那這些活動如果我們從體制上來看的話,可能是攸關國家主權、社會秩序,或者是民生系統,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那這樣的動態實踐下作為體制的邊界呢?它在運作上會進行,比如說篩選、監督和區分去決定說:我們怎麼定義自己,然後也去定義我們以外的人,那這個就是我談的邊界的概念。那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都是比較體制上面說這個邊界上的運作是在做什麼,可是邊界上面如果住了一群人,那這一群人他們的行動,比如說是很日常偶發的行動,他們其實也有可能是會脫離國家的掌控、脫離體制的掌控,然後甚至推進了這個邊界的移動或者是改造,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從這個角度來談:「流離島影」對「邊界」這個概念提出了什麼樣的理解。
不過因為今天放映的片子基本上就是跟金門,還有烏坵這兩個地方有關,因為金門跟烏坵其實地理空間是離得非常遠,就是你可以想像馬祖在最北邊,金門在比較南邊一點,然後烏坵就是在兩者之間。然後因為過去烏坵其實是屬於台中縣政府在管理,對,沒錯,這個沿革過程大家可以維基一下,anyways它後來被歸到金門縣來管理,可是其實金門縣離烏秋的距離非常地遠,然後這個也是一個盲點,那我們後面會再繼續分享。那首先,我想要先從這個時間表(投影片上年表)開始,那金門或者是沿海的這些島嶼是怎麼變成邊界的?這個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像是說1948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開始發生,然後國民黨軍向中國的東南沿海還有西南方撤退,所以金門、馬祖、南沙,和東沙群島先後被劃入戒嚴令的範圍。那接下來,幾場發生在金門,或者是馬祖這邊的戰事還有1950年到1953年韓戰的影響,更確定了金門和馬祖是作為前線島嶼的地位,所以在這個情況下,1956年頒佈的「戰地政務委員會條例」確立了金馬的全面軍事化的基礎。
那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說,是國共內戰的結果,讓金門和馬祖變成了邊界,而不是我們過去說他們是什麼天然屏障,比如說很大的山脈或是很大的河流,並不是這樣,它們一直以來,這些島嶼跟他們的沿岸城市是非常緊密的,而是因為在戰爭中,他必須變成邊界,那地理學者就會稱這叫做「意外的邊界」,因為這個邊界本來是不存在的。所以說這個情況下,金門和馬祖是要在時間中重新被「邊界化」,就是它本來不是邊界,可是現在要變成邊界,那要怎麼進行呢?首先在冷戰的語境下,金門跟馬祖,現在是被打造成「自由世界」的前線,然後藉此將我們和共產政權作出區分;另一方面,金門跟馬祖的全面軍事化不是出於戰略所需,就是不只是這樣,它其實也是藉此跟工業化、現代化,然後加入美日國際分工鏈的台灣本島做出區別。所以說這其實是兩重界線——一個對外,一個對內——這樣子的雙重邊界才奠定了中華民國在台灣本島作為戰後現代國家的正當性。那這方面的研究就是其實還蠻多的,關於地緣政治的,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查一下,我這邊就先講到這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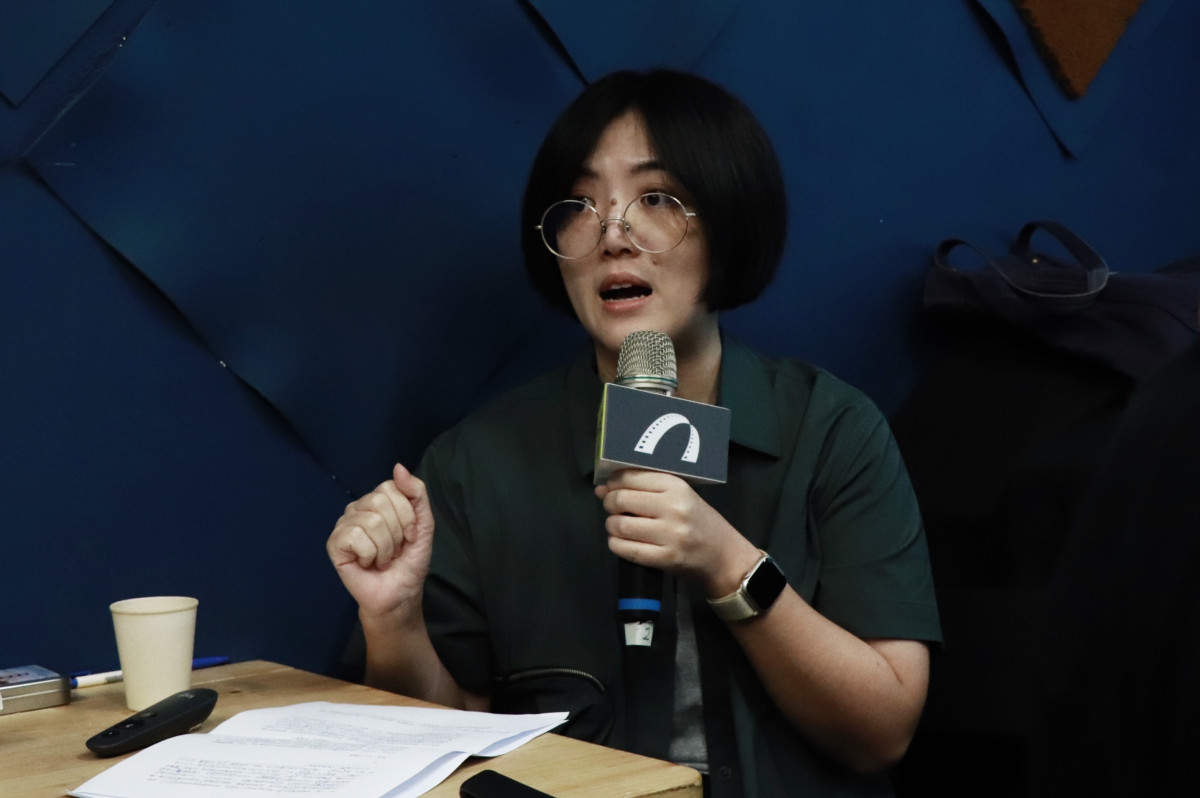
那更重要的就是軍事化作為一個邊界化的效果,它對金門這邊人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呢?除了戰爭本身——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看到在五〇年代、六〇年代還是有陸陸續續一些戰爭是實際影響,有一些死傷的狀況——那除了這種直接對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脅,其實軍事化更重要的是將軍事利益或是軍事的目的,變成本來跟軍事沒有關係的——比如說日常民生文化,或是經濟事務——的唯一指標。所以說軍方可以強迫民眾參加民防訓練,或者是說在教育上,他就是要一直說服你說,你做這件事情是為國家好,所以用這些當作一個說服你或是操控你的想法的做法,他就可以在,比如說燈火阿,或是出入境物資上都有很多嚴格的管制。而且在十萬大軍的年代,金門、馬祖的民眾收入其實是很依賴軍方那邊消費的,所以像是《03:04》中你們剛剛有看到嘛,就是那個雜貨店,它其實就是在軍營附近,然後就是阿兵哥他們可能稍微有休息的時間,他們就可以在那邊吃東西,然後耍個廢這樣子。那問題就是說這個互相依賴,可是其實又是壓迫跟控制的「軍民一家」的關係——我這邊舉一個我前幾天實際聽到的例子,就是我認識了一個40年前在金門當兵的當事人,他就跟我分享說那個時候他們要蓋水庫,然後他們的部隊就下命令下來說,你們每一個阿兵哥都給我搬一塊大石頭回來,因為金門這個地方雖然有一些山丘,可是其實這些建材是不夠的嘛,那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你給我去找大石頭,那並不是每個人都找得到大石頭嘛,那這種時候要怎麼做呢?這些阿兵哥就趁休息的時候,跑去軍營旁邊的雜貨店去挖別人的牆角,我聽到就說你們那時候沒出事嗎,就是怎麼都沒有一些聲音去批評這件事,他就說不可能啦,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就是不管你有沒有聲音,你最後都會覺得說,反正我抱怨也沒用——這就是所謂的「軍民一家」的概念。
那問題就是說軍事化它還是有一個盡頭,軍事化它還是有一個程度之別,當政治環境發生改變,大量駐軍不再有必要的時候,民眾的生活其實又會再次受到衝擊,那就是(投影片)下一個時間表,我這邊有列了幾個比較關鍵的時間,像是台灣開始開放對中國的間接投資是1990年嘛。那大家都知道1987年的時候,台灣已經解嚴了,但問題是台灣解嚴了,同時間金馬到底要不要解嚴呢?那個時候,國防部就說:好,我們先解嚴,我再下一個臨時戒嚴令,所以金馬又再第二次被戒嚴。然後金門、馬祖的人就覺得,為什麼就你們可以解嚴,我們為什麼不能?也就是說外部邊界可能已經開始慢慢鬆動了,但是內部邊界其實是花了又再五年的時間,是很多民主運動人士在奔相走告才好不容易達成的。因此1992年的時候才是正式的金馬解嚴,那問題是金馬解嚴之後呢?他們又再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爭取到金馬跟台灣之間的出入境管制直接解除,不然本來你還是要看身分啊。然後你帶了一些攝影機什麼的(設備),你都會直接被押走,像董振良導演他之前就是為了要拍片,結果他就背著攝影機,然後就被抓進警察局裡面關了兩天。
那剛才的片子剛剛好都不是戒嚴時拍的,我只是就是補充一下前面發生的事情,你們才會知道說「流離島影」它是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下(發起的)⋯⋯這就是接下來要說的,就是在這種時候,當金馬——這個對於台灣的內部邊界開始鬆動,然後兩岸關係也開始慢慢的要正常化的時候——就是在這個轉變的時間下,「流離島影」的計畫開始發動了。2001年小三通的啟動,更證明作為外部邊界的金馬,不再是絕對的防堵和對立,而是作為有彈性、可協商的邊界。同時,作為內部的邊界,金馬在台海危機之後,兵力部署也大幅縮減。雖然軍事上的迫切性減低,但遠離本島、人口少的地理條件,卻讓烏坵被相中,成為核廢料儲存的候選場址。
就是說,你一開始先是作為一個軍管地,然後為了去保護所謂的「大後方」你才會被軍事化,但問題是:當你沒有軍事化的必要性的時候,你作為一個邊陲島嶼的價值是不是又可以再次被國家體制利用?就是在這樣子的轉換之下,「流離島影」這個計畫才會變得這麼重要。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下「流離島影」。就是從這個脈絡來看,我認為流離島影去集結了13個影人,然後前往12座離島的拍攝計畫,其實是一個重新發現邊界的嘗試。一方面是他們直接去記錄了當時邊界上的生活跟事件,從無人島到地緣政治的這些前線,拍下這些在消息封鎖時代,對台灣本島的大眾來說,相對陌生的離島;那另一方面,創作者前往邊界的過程本身,以及這個過程中,邊界作為體制的邊界的運作,其實也變成紀錄片的一環。那舉例來說,在1999年他們出海拍攝的時候,其實台灣的局勢才回穩,那很多制度都還在發展的狀況下,要前往那種軍管地或者是已經被列入所謂自然保護區的地方你都要向海巡署,或是國防部申請,要走很多程序,然後確保你不會去觸犯到一些機密。在這種狀況下,比如說明天會放的李孟哲導演的《南之島之男之島》,知道他去東沙島的時候,就是一定要做國防部的軍機去,不然的話他就不讓你登島,其實到現在也還是這樣,東沙島到現在還是這樣子的軍管地。或者是像周美玲她去烏坵的時候,他只能用DV拍,他不能夠帶16mm,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有一個影像,說他一開始好像是用DV在拍,然後突然換一個鏡頭,然後你就看到它是用16mm帶去翻拍他的第一個影像,我覺得她也是很聰明,她利用了這個媒介本身它變成了一個製作條件,然後這個製作條件可以直接呼應到那個時代的狀況。然後像還有釣魚台好了,就是這一次的新竹站也會放映的《誰來釣魚®?》,釣魚台的狀況就是你不可能申請登島,所以他們花了10萬去租漁船,這10萬在那個時候他們這麼窮的狀況下,花了這個錢,他們一定要回本。很多政府單位啊,日本大使館都會打電話來,就是警告他們說,你們出海會出事喔,但他們一定要走,結果他們就出海了。所以你們接下來如果有看到《誰來釣魚®?》的話,就會看到他們前往釣魚台的行動,引發各方勢力到場監視和施壓——而這就變成了紀錄片本身的內容。
那我們剛剛其實都在講主權秩序運作這樣子的體制上的邊界,但其實對創作者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紀錄片的邊界。雖然周美玲1992年到金門日報工作,然後他後來就也跟著董振良拍了很多東西,那他非常了解金馬的議題,然後也很早就知道烏坵的議題,可是他從來沒有真的想過是要為了這些島嶼去做一些什麼,反而是他跟一群好朋友在他在雲河街租的房子,就是師大大公園那邊,台北市的四大公園那邊的房子,然後聚在一起喝酒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創作的話,以後就沒機會了,那要走就走!然後大家就是這麼酒後義氣相挺,他們決定要為了電影創作的熱忱,開始要推動這個計畫,而不是真的為了島嶼,那為了電影熱忱,比如說他們選擇紀錄片,是因為紀錄片是當時最對於創作者來說門檻最低的,劇情片是非常花錢的。那既然要做紀錄片,他們就開始看說,當時的紀錄片的製作方法或者是那個時候最紅的紀錄片是怎麼樣的。像可能大家現在已經不太了解,就是那個時候其實是吳乙峰跟全景工作室非常非常紅的年代,因為他們推動的就是那種全國的大巡迴,所以非常多人都是透過吳乙峰拍的東西去認識到紀錄片的,那他們代表了某一種長期蹲點或是弱勢發聲的典範,周美玲認為這已經變成某一種道德標準,好像你沒有符合這個道德標準,你就不夠格被稱為「紀錄片」。這些都無關創作者自己的實際的觀點,或是你的創作手法到底有什麼差別,所以說他們(「流離島影」主創)一方面前往邊界,是為了給觀眾不一樣的體驗;另一方面就是從影像來說,要帶領觀眾進入這個陌生的領域,那剩下的(影像美學的部分)就是明天講座的內容。
所以總結來說:首先,就是他們拒絕從「島鏈」或是「前線」這類的地緣政治的修辭來理解他們看見的島嶼,因為這些詞彙其實預設的是台灣中心或是軍事化的邏輯;那再來就是他們的創作共識是,對於一個地方的觀點都必須建立在創作者的親身經歷上,無論是實際的觀察,還是出於夢境幻想或是心理層面這樣融入主觀傾向的。這其實也是當時紀錄片的蠻重要的特色,那在「流離島影」之前,其實也有像比如說吳耀東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還有就是這一次新竹巡迴也會放的蕭美玲的《斷線風箏》,然後蕭菊貞的《紅葉傳奇》然後再隔一年就是《銀簪子》。這些其實都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跟前面世代試圖做出差異,這個最大的差異就是,這一代的創作者他們拒絕或是放棄成為某個領域的權威,他們不急於遊說觀眾,也不馬上為影像向下定義,而是誠實地面對自己身為一個紀錄者:我的侷限是什麼?那這個侷限其實才是他們去探問他們想要關心的東西的出發點。
所以說「流離島影」是確實意識到舊的邊界還沒有釐清,但新的邊界正在崛起的過程,比如說包含金門、烏坵、馬祖、東沙,還有北方三島,這些曾經都是,或是現在仍然是軍管地,可是「流離島影」是在跨境交流,還有國家保育體制介入之前,就拍下了軍事化和地緣政治遺留在島嶼上面的痕跡,還有對人的影響。「流離島影」交出的紀錄片就是每位創作者對於邊界的表達,那我不會說他們每個人的觀點都很有啟發性,也不是每一部都是傑作,可是我可以統整出他們的一些思考傾向,就是無論是實體的邊界,還是作為隱喻的紀錄片的邊界,都是他們對時代體制還有影像典範的回應。
那另外,就是剛剛前面提到的核能發電跟核廢料處理嘛,那其實這是一個從戒嚴時代、七〇年代就一直構成的一個犧牲的體系。我這邊是用高橋哲哉的概念,那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本書的介紹(《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2014年,聯經出版)。總之就是這個體系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在降低軍事化之後,反而讓烏坵成為繼蘭嶼之後即將被國家給剝削的邊陲島嶼。所以說從這些考慮下,如果我們再去看我們今天看的這兩部片的話,我們要怎麼理解我們看到的東西?這就是一個我覺得有比較多詮釋的空間,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解讀給大家聽。
那首先,我幫大家介紹一下,《03:04》的製作背景。黃庭輔在這個13個人裡面,其實定位是比較不一樣,就是這13個人裡面,除了黃庭輔跟許綺鷰以外,其他人都是從台灣本島出生的,黃庭輔是金門出生,然後許綺鷰是澎湖出生。那黃庭輔的話,他其實是在金門出生,到12歲之後才因為哥哥的醫療問題,然後全家搬到台北,那時候還是單打雙不打的年代,大概是七〇年代初的時候,所以他下一次回到金門的時候已經是解嚴了,然後解嚴之後他已經成年,而且也開始拍片了一段時間,他面對的是軍隊開始撤軍,人口也大量外移之後,完全不是過去的軍事境地,反而是已經荒廢沒落的家園。所以他將鏡頭轉向這些在街頭上遊蕩的老人、流浪犬,還有在雜貨店就是發呆、打瞌睡的軍人,那他沒有用任何的言語的敘事,包含說他沒有去訪談這些人,也沒有加任何的解說,旁白只有用你們聽到的那個類比噪音的實驗音樂,是廖銘和做,的,然後拉開觀眾跟影像的距離,讓這些動作緩慢、沒有生氣,好像不為任何任務驅動的身體變成了電影的主角。
但是在進入分析之前,我想要在繞回來談一下,金門的影像其實一直以來都有而且還不少,跟馬祖或是其他離島來比。所以金門之前的影像比較多是美軍還有官方製作的一些新聞片和紀錄片,那這些網路上其實很多都是公開的,那這些紀錄片可能會解釋當時正在發生的戰爭背景,比如說八二三砲戰啊,還有就是六〇年代美援進入金門之後,有一些長官、貴婦們就跑去金門做一些什麼訪查,然後就是感謝一下他們的付出之類的。那這個時候主要是這樣的內容,比較特別的是中影和日活合製的《海灣風雲》(1962),他的日文的片名「金門島にかける橋」其實就是「通往金門島」。雖然故事上和金門直接相關的段落不多,但它將二戰造成的陰影,連結到金門八二三炮戰,是滿有深意的操作。不過,長年以來,金門影像總是關於戰爭或軍事部署,直到90年代,董振良拍攝一系列混合紀錄片和劇情片的電影,拍出解嚴前後,金門的民主化抗爭,還有戰地政務下,金門人民的生活經驗,這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歷史面向。所以相較之下,黃庭輔的影像其實是在這些層面上又更激進了一點,他的影像著重的並不是敘事性的,他沒有要跟你很急著介紹說金門是什麼樣子,他只掌握某一個氛圍,讓我們可以看見那個氛圍的,其實就是影像中的身體。
好,那現在你們看到的這一段話:
老人等待一副好棺材、小孩等待快快脫離島嶼、阿兵哥數著饅頭等待退伍、老兵等待發薪再來預支老米酒、小狗徘徊門檻等待阿婆溫慈的眼神、而老闆娘等待股票漲停板、老闆等待無憂的退休金、小鳥等待不再有的高粱穗......樹等待風、風等待石、石等待歸人、而我等待電影的結束。
其實是他寫在他們有出一本(拿出書)介紹他們的創作脈絡的一本書(《流離島影》影像書),大家等一下可以翻一下。那這段話你們可以看到,他就說「老人等待一副好棺材」、「小孩等待快快脫離島嶼」、「阿兵哥數著饅頭等待退伍」都是「等」,「等等等」,那這一段話提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等待」,其實也是表現了當時的黃庭輔眼中的金門人們待在這裡是為了離開,或者是等待終結的時機到來。一方面,人就像存在這個環境中的物件,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他寫道「樹」、「風」和「石頭」,然後電影裡面,則是有比如說放在雜貨店裡面的時鐘,然後日曆、蒼蠅拍、貨架,和冰箱這些都是很孤立的物件。他刻意不去拍那些人在使用這些物件的時候,而是讓人跟物件好像沒有關係,他們都是沒有被使用,沒有被賦予任何意義的情況下出現在影片裡,然後單純存在這個環境裡面。那另一方面,我們去理解所謂的「等待」的這個狀態,意味著說,在等待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在等待的,它有一個過去存在,可是等待之後,它其實也是為了某一個目的,然後去指向某一個他要去實現的未來。意味著說,在過去和未來的交會,「等待」本身也是一段時間,然後在這段時間裡面,人怎麼去表現那樣子的身體狀態,其實也可能反映的是人的感覺或是精神的、他們的想法。所以說,這些東西就變成我們可以觀察的對象。問題是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這種所有東西——不管是人還是物——都進入一個共同等待的狀態呢?那從實務上來看,我們剛剛有提到台海危機之後,大量撤軍人口移出,可是金門從來都沒有真正地完全地「去軍事化」,而是讓軍隊維持在最低限度的部屬,那留下的居民其實也維持過去的經濟模式。比如說,就是他們可能維持這樣的模式,某方面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某方面也是在預防下一次的危機再次出現,就會有需要他們站在那裡的時候。
那坦白講,我大概十年前第一次看《03:04》的時候,我在想這個等待到底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我會很單純、很自然地完全不需要多想,我就說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你怎麼等都等不到的等待。可是那是因為當時的我完全不相信台灣還會有戰爭,可是如今我再回頭去想我當時寫的東西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在思考的東西已經有點不太一樣,我可能是到現在才真正開始體會金門人的感受是什麼,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可能不會說這樣的等待是沒有意義的,而是喪失了原本的目的,但是新的目的還沒有進入金門的狀況,這是我的新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學者宋怡民(Michael Szonyi)其實有提到過,他在那邊做了一些田調,當時經歷過這個軍管時期的金門人,他們面對日後轉型為歷史觀光財的戰爭記憶通常會採取就是比較懷舊阿、英雄式的論述,去緬懷當時這些阿兵哥,這些參與民防系統的平民,他們有多勇敢。可是問題是這樣子的論述,其實是將過去被壓抑的那種苦難,轉化為某一種替國家犧牲的自我認同,所以它其實是一種變成歷史創傷,那這種歷史創傷的徵候會怎麼顯示在金門人身上?其實就是當他心裡其實還困在戰爭跟軍事化的陰影的時候,他們會內化這樣子的愛國論述,然後一直在強調,自己仍然在這裡的重要性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跟正在向內凝聚的台灣的共同體,慢慢的拉開一段距離,甚至是他們跟下一個世代的金門年輕人,這些年輕人不管是擁抱中國的經濟,還是也加入台灣這個共同體的思考裡面,都會跟前一代的人拉開一段距離。所以我認為《03:04》去展現了這種共同的等待,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時差」,也就是說,過去長期佔據身心的國家逐漸抽離的時候,留下來的影響今天還是用不同的方式,仍然持續的支配這個地方。比如說《03:04》也透過鬼魂或是死亡的意象,來強調戰地歷史的陰魂不散。像是你們看到很多,就是這種隨風飄動的衣架,或是就是在那邊翻動的日曆,或者是你們應該也有看到一些很像在戶外做一些儀式,那其實就是金門特殊的王爺信仰,然後金門也有軍神信仰,就是以當時就是比較有名的軍人的狀業,赴死就是那種烈士的概念,然後去做的那個小廟,就是希望他們的靈魂可以安心不再去打擾這邊的平民。可是這些鬼故事啊,或者是平民,他們每次都會覺得自己的家裡鬧鬼,這些事情都還是存在在他們的生活之中,那這些都是黃庭輔之後拍金門的紀錄片,比如說《不在》,還有最近最新的《無.無明記》(2025)有更多的詮釋。那在這邊的話,他比較像是一個開端,去想這個鬼魂跟死亡,還有金門的風景的關係是什麼。

好那接下來就是周美玲的《輻射將至》,我認為它開出了邊界的另外一種面向,也就是這些參加反核廢抗爭的烏坵居民,雖然都是很不願意讓核廢料就是放到自己家嘛,但問題是,他們在面對這個台電提出來的探勘的時候,他們又會想到說,我其實可以把這個兩岸關係來當作一個槓桿,就是我一手拿探勘費,然後一手在賭中共會不爽。那問題就是說,這個同時也是說,有村民可能聽到這種事情就會覺得,這個又是國家要欺負我們,然後即便是民主化的時代,由於烏坵仍然是軍管地,所以民眾其實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然後日常民生啊,包括日用水都是一直靠軍艦運輸,直到現在烏坵還是靠軍艦運輸他們的日常的吃喝的東西。所以說,過去戰地政務時期的意識形態教育其實也會加強人民深信,自己的抵抗,或是自己想要去做出的改變都是沒有用的,那這種無法自主決定的心態,就是當時的狀況。可是「永保烏坵」這種說法,這種愛國的說法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沒有說服力了,所以說他們既認知到邊界對國家運作的重要性,即便是在那樣子的內外邊界都在動搖的狀況下,問題是實際上在邊界的生活,其實總是需要和不同的勢力,不管是利誘威脅,還是合作,這些都是要進行協商的,這就是一個邊界上的生活的狀態。我覺得周美玲她就是蠻精彩地去抓住了這一點。
那另外就是在訪談之外,電影也利用取景的角度,還有溶接、多重曝光這些手法,去疊合不同的元素,比如說台電探勘的時候,他可能會有一些紅布條的影像啊,她就故意把它疊在那個蔣介石的那個背影,軍管時代還有刻在紀念碑跟房屋外牆的那些標語,她也會刻意去跟那個他們那時候為了反核廢掛上那些布條去做一些對比,就那些課在牆璧上,好像永遠都不會腐朽的標語相較之下,一、兩前才剛掛上的法規跟標語已經變得很舊,然後掉到地上,都沒有人去處理,這邊其實都強調了,烏坵納入核廢料處置這個犧牲體系,其實就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延續。那前面我們提到內部邊界就是島嶼的軍事化,然後去換取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嘛,但問題是,這之後島嶼它的軍事化變成了某一種特殊化,「特殊化」,你終究還是為了某一種所謂的「台灣的公共利益」、「多數人的公共利益」,然後讓邊陲島嶼的犧牲變得合理了。這也就是為什麼片中的蔡老師會一直要說服村民說你們不要去收探勘費,就是如果你敢把加入體系變成一種賭博的話,你在賭的東西其實是你本來就所剩不多的東西,就是你實際住在這裡的這個事實,如果你把這個你所剩不多的本金壓在上面的話,你未來其實會更難從這個系統裡面脫身。
那比較可惜的是《輻射將至》他其實還是聚焦在烏坵嘛,他沒有把蘭嶼的這個題目拉進來,可是烏坵當時為什麼會被選為這個處置地也跟蘭嶼他們在反抗他們作為一個中繼站的這個脈絡是有關係的。因為蘭嶼大概是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有很大的一系列的反核的抗爭。那台電因應的作法就是,好,那我要再去找一些地方來放這些東西好了,那他找了什麼樣的地方呢?比如說花蓮縣的富里鄉,然後屏東縣的牡丹鄉、台東縣的達人達仁鄉,或是馬祖的東莒島。那這些地點的共同特徵是什麼?其實就是遠離政治經濟中心,而且很多都是在原住民的土地上,所以你就是把一堆核廢料從一個原住民的土地上拿到另外一個原住民的土地上,那這就是一個地理位置和族群上的雙重歧視。就是我們可能會不知道的是台電在2002年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放棄烏坵了,因為當時烏坵還是有引起一些爭議,可是烏坵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就像蔡老師說的這事件還沒有落幕,因為烏坵的問題在2020年的時候,其實又因為台電跑去金門辦了一系列的說明會,然後又被吵起來,那時候就有人在討論說,金門這些遠離烏坵、從來都沒有去過烏坵的這些金門人,有權力辦公投來決定烏坵要不要放核廢料嗎?這些議題是2020年那時候有吵起來,可是金門人也是懂烏坵的狀況是什麼,他們也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做這件事,所以他們其實都也很反對台電當時的這些想法,所以又引起了一些爭議,最終是到現在都還沒有結論,東西都還是在藍綠這樣子。
那順著說下來,我們可能會想問的是,真的沒有⋯⋯就是現實中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沒有犧牲的體系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就是當核災的這些這一切都變成一個大爛賬的時候,我覺得要實現不是不可能,可是我覺得這會變成一個共同去努力的目標。那問題是,電影創作或是紀錄片在這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其實從「流離島影」的例子來看,我認為前往邊界的行動,其實首先就是看見我們現存,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由島嶼串連互動而成的群島國家,我們從來都不是依附本土大陸的零碎空間,我們不是土地很小的、小小的國家,我們是一群島嶼串連而成的。那另一方面是誤打誤撞,「流離島影」某方面來說,也展示了島嶼之間在地理、生態,還有歷史上面的共通性,所以我可以說每一個島嶼都不是以前軍管時期他們會強調的「我們是一個孤島」、「我們很勇敢,島孤人不孤」⋯⋯可是從來都島嶼都不是孤獨的,每一個問題也都不是單一案例,而是環環相扣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覺得「流離島影」不只是看見地緣政治下面實際的島嶼空間,它還介入了過去某一種前線/本土、邊緣/中心,這種二元敘事,他去正視的,是這個壓迫跟犧牲的體制,然後去看見體制中的人,包含身為紀錄者的自己。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其實到現在是變得更迫切的,就是在他們那個時候可能很多事情開始鬆開,大家的心態也開始轉變,但我們其實現在也在面臨的一個身體又開始繃緊,然後時局也開始改變的時候。那我覺得我會想的是,我可能會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狀態吧:我的身體是怎麼反應這個變得緊張的時局?然後未來我又該怎麼做才不會重蹈覆徹?這是我想可以等一下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的話題,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主持人
很感謝正媛,剛剛非常精彩的分享,就是相信大家對於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啊,或者是對於要怎麼樣看這些作品又有新的一層想法。那因為還有一點時間,我想要先看看在座的觀眾有沒有任何問題想要問。
Q1
想請問一下,就是剛剛有提出那個中心跟邊陲的思維,然後就是這個「流離島影」的核心概念,就會從一個犧牲的體系去對這樣子的一個中心思維提出一個抗議。但是就是在此同時,它是不是又更強調了就是一個中心跟邊陲的二元這樣的關係?那事實上就是說,在他們提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群島的概念裡面,其實它已經有一個非常朝向海洋跟未來,然後多元,是像地下街一樣水平串聯這樣子的一個途徑,那但是就是說,在他們對於影像的這個形式的實驗,也是非常地勇敢在當時,但是他們對於就是這個,他們已經做到一半的本體論或是史觀,其實還是用一個比較隱喻,或者甚至是比較詼諧、去嘲諷的、很含蓄的方式去處理,那其實這些導演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勇敢,就是都是一時之選,那就是不知道說作者/老師,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趙正媛
我覺得你說的就是完全正確,我覺得這也可能是我自己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吧。我覺得,哇天啊,你們已經這麼早就已經想到這些事情了,可是事實上他們真的當時一心都只是在說:喔我要搞創作,我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紀錄片,他們其實真的沒有想得那麼複雜,我覺得這是最遺憾的地方。可是我自己會用不同的角度去想說,即便他們本人講出來的話,有一些其實你看了還是會覺得他還是一個很台灣的某一種對島嶼的偏見,因為畢竟我們光是講出「離島」這兩個字的時候就有問題了對吧?對,所以就是我覺得他們可能並沒有完全地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或是他們去擅自拿島嶼作為一種隱喻,而不是就是實際地去看見這個島嶼,它的這些更複雜的層面,我覺得他們本身,他們絕對還是一個很台灣本島受訓練出來的人,他們的有限思維能夠做出來的大概就是這個狀態。可是如果我們不是從他們本人直接說了什麼,而是去看影片發現了什麼,有一些影片拍出來的東西,可能是他們自己沒有想過可以又再被重新拿出來討論的,所以我剛剛會講到滿多說,為什麼我會認為它還是一個發現邊界的過程,就是我覺得不只是實際上你到那個地方,而是說把它變成一個主題。而且他們可能某種程度上為了要讓自己的作品發揚光大,所以搞了非常多的放映活動,然後還去南藝大踢館啊之類的,他們做了非常多事情去放這些影片,然後我覺得這在當時就有一種帶出一個效應是,欸好像大家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了一堆島嶼的敘事,突然都跳在大家眼前,就算它一開始的動機不是為了島嶼。
Q1
(續Q1並回應趙)南藝大踢館那個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因為吳乙峰那時候在南藝大,所以他們好像預設就是南藝大就是一個當時的紀錄片典型的一個大本營,但是他們就是,尤其是那個,我們這次選的影片就是那個周美玲的烏坵,她其實還是在回到一個,幾乎比這個吳乙峰的典型再更古典的一個,就是紀錄片作為一個道德喉舌這樣子的一個任務型的、先知型的一個提問者。對,那所以我覺得他們事實上已經做得比他們自己發現的,或者是自己給自己的任務,還要在更前面的,但是這可能是就是一個創作者的直覺吧。
趙正媛
沒錯。
Q2
因為其實像你剛才談到的這個犧牲體系啊,那個也是Takahashi Tetsuya在福島之後才趕快寫出的這本書啊。那也就是我其實對這些影人啊,在2000年,你剛才講到兩個重點,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他們要拍攝紀錄片,基本上他們花了十幾萬,也算很多了啦;那第二個我覺得比較矛盾的就是,你剛才提到這些人,其實不想成為紀錄片這個領域的權威⋯⋯(趙正媛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錢砸下去了,然後再說不想成為權威,回來之後,當然那個要回本,我認為是⋯⋯至少拍的這些東西⋯⋯所以你剛才提到的,他們也是非常努力地全島巡迴,當然那時候因為我對2000年那時候的背景,應該是說2000年算是1999年,就是921大地震,然後又Twin Tower 2001年嘛⋯⋯然後這些影片差不多就是就是在這兩個事件之下,然後很快的又SARS、台灣第一次政黨政黨輪替嘛。所以我覺得那個氛圍的確有一點像2013年的烏克蘭。所以我其實不太理解,那這幾年在紀錄片啊,你可以稍微幫我們講一下,那時候在本島啊,其實在那個巡迴,我猜你研究應該還是會有那個巡迴,就是群眾看到這些離島,尤其他們在挑戰的一種「啊!不民主啊!」大家其實那那時候都一直在挑戰「到底民主⋯⋯(是什麼)」,這很明顯嘛⋯⋯這件事情由不的人民嘛,但是現在的人普遍都相信,我出生就是民主⋯⋯ 就是那時候在巡迴的時候,那時候的背景,2000年初期。

趙正媛
你剛剛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他們明明不想要成為權威,可是還是渴望自己的作品被看見嘛?(Q2觀眾:我沒有講錯吧?)恩⋯對,這個可以聊一下。然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們在巡迴的時候,在這些脈絡下面,那觀眾的反應是什麼,我可以這麼理解嗎?(Q2觀眾:對,因為那時候最夯的還是蘭嶼嘛)
其實蘭嶼那時候已經稍微有點退燒了啦,就是那個話題已經沒有那麼在勢頭上面了。我現在先回答權威的部分好了,就是我看了很多他們不管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訪談,就是國影中心他們有一位老師以前做的碩士論文,陳德齡有一個很完整的訪談,那個應該會是最第一手的資料啦。就是他們當下在想的問題,就是他們那時候再去考慮這個權威的時候,其實是在想的是在更早之前的紀錄片,或者是某一種,就是所謂的吳乙峰或全景,他們下來的這種紀錄片,他們會很強調,有一個就是充滿愛、充滿關懷,然後對於這些議題,真的很用心去鑽研的這種位置,就是有一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就他們會其實是會一直頻頻地讓拍攝者入鏡,然後去展現出他那種親力親為,然後很努力去接觸這些受傷受得很慘的人的那種畫面。可是他們(「流離島影」計畫)在質疑的就是這一點,就是你是誰?然後為什麼這部紀錄片的重點變成你去幫助這些人?然後好,你不入鏡就算了,如果你拿這些鏡頭去人家家裡面,就算人家有話想要說,可是你有考慮過那些人被拍到之後,他們要付出的就是不管是社會輿論的關注,或者是他們在自己的家人生活工作之間,那要怎麼去面對這些東西嗎?
觀眾
921吳乙峰拍很多這樣的東西。
趙正媛
他那個真的拍得蠻爛的,說一句真心話。反正就是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流離島影」這一群人,他們要做的就是這一點,就是我不再假裝我是一個什麼事情都能夠照顧到的人了,我不再假裝我是一個沒有私情,沒有醜陋的內心,沒有那些慾望的人,他們反而是把這一點拿出來,然後有一些片他們會很直接地去反省這一點,這個我們明天放映的《噤聲三角》是走地最激進的,歡迎大家來看。然後讓他們放棄去成為某一種理想的,佔有某一種道德高位的就是拯救者或是指導者的時候,這就是我所謂的,他們不願意去成為那個權威。他們跟我們在座的觀眾一樣,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私,那這些生活跟自私面的東西,這些就是很不成熟的旁白或是什麼也好都會丟出來,然後讓觀眾來決定我是什麼樣的人。但是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其實也是很不成熟的,就是有時候你把這些未經思考的衝動也好,不管是什麼也好丟出來,其實也可能是一個對當事人來說不太好的狀況。
但問題是他們想要先破除那一種好像我跟觀眾有距離、我跟觀眾的差別就在於喔我真的有接觸過這些受害者,然後我真的做了很多研究,他們不會去擺這種姿態。所以他們當時去巡迴的時候當然就是大家都在問啊,那時候大家其實也沒那麼關心島嶼,那時候大家就是看了,OK那你這個影像形式很特別,說說看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形式,他們光是要去解釋「這算紀錄片嗎」,「可不可以就叫這個叫紀錄片」,「如果這個不是紀錄片,那會是什麼?」他們會在意這種定義上的問題,糾纏非常地九,所以他們有時候是甚至是會更輕鬆一點,比如說正在放映,然後他們可能有一些導演,當天輪班就在門口坐在那邊,賣票、賣一些周邊,然後也帶一些他們去離島買的那些零食啊、飛魚乾啊,什麼貢糖之類的就擺在那邊,然後請大家來吃飯啊。然後(觀眾)可能看完看一看覺得很煩地走出來了,就說欸這你拍這什麼東西,然後可能就會用這種很輕鬆的(方式)就這樣開始聊,然後這些導演他們也不是那種很極力推銷說我的作品怎樣怎樣,我做了什麼什麼的。他們是(反問觀眾)說那你覺得我拍了什麼?你看到了什麼?把問題丟回去,讓觀眾去想,他們希望觀眾是一起進來討論,我拍了什麼,然後為什麼我要這樣拍⋯⋯然後這些其實都是,怎麼說呢,讓紀錄片本身被看見,讓這些議題本身變成我們這些平凡人沒有人要教育誰,沒有人要知道誰,我們就是一群人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主持人
好的,剛剛的討論非常精彩,但因為時間的關係看看有沒有最後一個提問,想有人要發問的嗎?好像暫時沒有,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想有任何事情想要請教正媛或是想跟她聊的,都歡迎等一下可以私底下跟她輕鬆聊聊。
然後最後我來宣傳一下,就是剛剛我提到的那個《Fa電影欣賞》雜誌,我們後面都有雜誌的實體,那大家如果想要翻閱或是想要在現場購買的話,也可以直接購買,那裡面是有一個「流離島影」專題,然後裡面有正媛的文章,然後以及他剛剛提到的那個研究者陳德齡的文章,一個完整的六篇的專題。
那最後一件事要提醒大家,就是因為影博館7月26號會休館,所以我們有一些場次有調整,那這個調整大家可能就要上我們的官網或是社群看一下,就是當天不要不小心跑過去。好,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