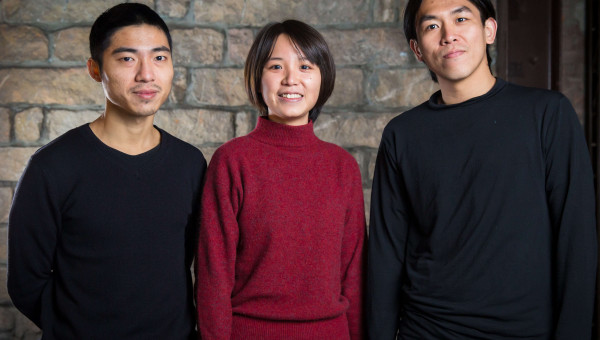敬那些看不到卻默默跟著我們、看著我們的人——專訪《透明世界》顧問妮娜.庫策夫

《透明世界》(Transparent World)記錄有點「不一樣」的貝卡(Beka),他有著自己獨特的人生觀,並在父親的鼓勵下拿起了攝影機,渴望完成一部電影。在劇本的發想、拍攝的過程中,父子兩人對電影的想法總是有如此大的差異,他們時而合作無間、時而爭吵崩潰。而被攝者對拍攝地拒絕、各種突如其來的情況,都讓貝卡幾近崩潰邊緣。
影片不斷地揭示拍攝的過程與衝突、困難,但卻也看到兩個人的努力,父子倆的感情深刻體現。他們拍了什麼從來不是重點,重點是過程他們怎麼去拍攝,怎麼去溝通和怎麼去爭吵、去了解。
Q. 導演與貝卡一家是怎麼認識的?當初為何想拍這部片?
導演瓦多.庫策夫(Vato KUNTSEV)是貝卡父親的學生,在貝卡生出前就認識,已經有二十多年。當初貝卡出生時,因為基因突變醫生非常不看好,建議將貝卡留在醫院,但是貝卡父親不理會醫生的建議,決定將貝卡帶回家自己撫養照顧,現在他已經26歲,父親不僅是貝卡的老師,也是他唯一的朋友。
我們與貝卡一家交往很密切,在接觸中我們發現貝卡有著很特別的個人哲學,於是開始進行拍攝,藉由這一年多影片拍攝時的接觸,我們漸漸了解貝卡。我們發現貝卡是一個天才,不過由於他不穩定的情緒,一般不瞭解的人,不想跟他做朋友,就像貝卡在影片中說的柳丁與大便的笑話,我們因為社會環境的影響,經常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忽略了內在的本質,我想東方人應該更能瞭解內在比外在重要的這個道理。這部片的內容著重在貝卡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兩人相處的過程,主要想呈現的是,全世界父母親的愛,無條件的愛,「因為存在,所以愛。」
Q. 片名《透明世界》中所說的透明具有什麼意涵呢?
貝卡其實是個很有自己想法、有一套自己人生哲學的孩子,在片中,貝卡說道:「我的人生觀是,如果你透過手看太陽,手是透明的,我覺得看每樣東西都樣像看太陽,一定要看到透明性,這樣眼中的世界才會透明,我們才會成為透明世界的一部分。」我覺得,若只看外表,也許沒有人會想跟貝卡說話,但內在的東西往往比外在的東西更重要,若能穿過外表,看到一個人的靈魂與本質,那就能看到真實的世界。
人們常認為只有小孩與聖人才能一下就看到那些內在的、本質的真正世界,長大被社會化後,我們就會受到政治、宗教等影響,看不到本質。這個世界有許多事都是語言無法描述與解釋的,需要人去感受。
在片中,貝卡說了個關於柳丁與大便的笑話:「有個柳丁滾下排水管,遇到一坨屎。柳丁開始炫耀道:『瞧瞧你,是一坨屎。』屎回答道:『拜託,我昨天還是個柳丁』」,這個笑話其實與蘇聯社會的快速變化、快速流動有關。在蘇聯,生活充滿偶然與不確定,今日的大人物,明日的無名小卒。若不重視一個事物的本質的話,那就容易被快速改變的外表所蒙蔽。
Q. 導演在貝卡拍攝茶杯時結束這部影片,用意是什麼?
在構思影片結尾時,導演也曾考慮是否等貝卡影片完成,或是展覽後。但導演自求學時期,便不斷以各種實驗手法,嘗試讓影片呈現出更好的效果,相較於一般影片這個不一樣的結尾,其實有一個哲學意義。我們可以看見貝卡在影片中慢慢地成長,而最後遭遇的困難是個高峰。拍攝者不讓我拍怎麼辦,難道不拍了?最後貝卡自己想了辦法來解決問題。而遭遇困難並且突破,這就是貝卡成長為一個大人的象徵。同時「遇到狀況進行調整,找到目標繼續前進。」這也正是導演一直以來的理念。
Q. 《透明世界》拍攝完成後,對貝卡、對他們父子間的關係有沒有什麼影響?
剛拍攝完時,導演其實剪了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將許多貝卡情緒較不穩定的部分拿掉,較為溫和,後來統一只放這個版本。當時是先請貝卡的父母一起來看,看完後詢問他們的意見,看是否貝卡能接受。在觀看時,貝卡的父親數度激動落淚,因此許多時候不得不暫停。
而當《透明世界》在2018高加索電影節(CinéDOC-Tbilisi)獲獎(FOCUS CAUCASUS AWARD)的消息傳回至貝卡父親耳裡時,他激動地哭了。在高加索的文化中,父親常是負責賺錢,與孩子的親子關係其實是很被動的,母親多擔任主動照料的責任,但在這部片卻很不同,雖然貝卡有點特別,但他的出生卻成為父親的生活重心與新目標,為了貝卡,身為導演與教授的父親幾乎二十四小時與貝卡在一起,去大學教書時貝卡也會在課堂充當小助手。而當《透明世界》開始拍攝時,貝卡的生活就變得十分忙碌、充實,對他而言這便是個讓他活下去的意義。因此,《透明世界》的拍攝以及後來被肯定,對貝卡而言都像是在推進著他、鼓勵著他的生活,告訴他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