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講座|當時間開始呼吸:紀錄片在緬甸
時間:05.15 WED 19:30–21:30
地點: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102共享吧
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鍾適芳
與談人:
瓦旦電影節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監製 杜篤嫻
瓦旦電影節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導演/監製 泰狄
TEN MEN創辦人、《十年緬甸》導演 翁明
Tagu Films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製片 林孫烏
《吟唱靈魂之歌》導演 賽諾康
3-ACT創辦人、《蟻生幻夢》導演 莫妙玫札奇
譯者:錢佳緯、鄒德平
主持人
我是鍾適芳,今天很榮幸能夠擔任這場活動的主持人。
某些情況而言,緬甸似乎跟台灣的距離並不遙遠。譬如說在中和就有緬甸街,代表台灣跟緬甸之間早在1960年的時候,一些緬甸華僑就在台北的近郊落地生根。他們也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文化跟經濟的面貌跟景觀,在街上可以看到混合中文跟緬甸文出現,包含像是趙德胤導演青少年時期就到了台灣。但是我們從這個五百公尺長的緬甸街中認識到的緬甸,可能只有香料或者是特殊的風味等等,卻沒有涵蓋很多緬甸的其他面貌。
今年TIDF,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緬甸紀錄片,橫跨不同的時期、了解不同的區域。也讓觀眾有寶貴的機會看到跳脫官方的論述跟敘事的26部精選緬甸紀錄長片、短片,劇情片和實驗電影等等。

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到來自緬甸的六位影人一起參加。在我右手邊的是杜篤嫻,她是瓦旦電影節的共同創辦人,這也是緬甸2011年成立的第一個獨立電影節,同時她也是《十年緬甸》這部作品的監製。旁邊這位是泰狄,泰狄也是瓦旦電影節的共同創辦人,同時也是《十年緬甸-九重葛之城》的導演。接下來這位是翁明,他是TEN MEN的創辦人、獨立電影人,他們在緬甸舉辦各種不同的工作坊,他也是《十年緬甸-寄宿屋》的導演。在翁明旁邊的是林孫烏,他是Tagu Films的共同創辦人。Tagu Films是一間獨立的電影製作公司,希望透過紀錄片、短片的形式來敘述緬甸的故事,他也是《十年緬甸-親吻行動》的製片。林孫烏旁邊的這位是賽諾康,各位可能都已經看過賽諾康導演的作品《吟唱靈魂之歌》了,他的作品也是今年的競賽片之一。旁邊這位是莫妙玫札奇,她是3-ACT的創辦人,這個社群希望能夠促進影像教育及影像敘事,她也是《蟻生幻夢》的導演。
歡迎今天這麼多位緬甸影人出席。那首先,我想要先請在座的各位簡單介紹一下各位跟緬甸獨立電影社群之間的關係、自己的背景,還有歷年來所專注的議題等等。
杜篤嫻
大家好,我是杜篤嫻。我是瓦旦電影節的共同創辦人,之前是紀錄片導演。我從2005年開始做紀錄片,我的作品其實當時沒有機會在緬甸放映。2008年我獲得獎學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念碩士,因此參加了很多的影展,比如說柏林影展等等,我意識到影展並不只是放映的場合,還有很多交流的機會。當時泰狄也跟我一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念書,我們也因此去了很多歐洲的影展,有機會把不同的作品帶到緬甸播映,所以我們在2011年成立了這個電影節。我們的電影節總共營運了十年,2020年的時候舉辦第十屆,辦完第十屆之後電影節就停辦了,主要是因為國內發生政變的關係。
泰狄
我叫泰狄,我也是電影導演,主要是以攝影的工作為主。因為在舉辦電影節的期間非常忙碌,辦工作坊等等沒有太多時間做自己的創作。《十年緬甸》這部作品讓我有機會能夠再度在2021年的時候進行拍攝和創作。那我自己作為電影人,也做各種不同的工作,籌辦影展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TEN MEN創辦人、《十年緬甸》導演翁明)
翁明
我接下來會用緬甸文發言,然後再請林孫烏幫我翻譯。我是醫師,在學醫的時候我也有很多寫作的經驗。在這個期間,我對於寫作產生很大的熱情,所以我透過寫作來表達自己。 2007年我參加了一個工作坊,讓我意識到電影跟影像可以讓我用很不同的方式來說故事跟表達自己,也因此從文字轉向到了影像創作。我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興趣、不同的熱情,像是我會寫跟藝術有關的內容,一些表演藝術等等,其實真的算是蠻跨界,用不同的方式來訴說我的故事。那來到台灣,我也可以看到台灣有不同的博物館、不同的藝術、不同的媒介等等。而且每次看到年輕人,真的都可以啟發我用不同的媒介來說故事。
林孫烏
我一開始是有點意外的當上電影人。我是在美國讀書的,一開始我是讀哲學,甚至想要當律師。可是後來我發現美國的法律學院真的很貴,我不想要花這些學費讀完四年。回到緬甸後就在想我要做什麼,後來運氣很好的是,2012年時緬甸舉辦了第一次民主直選,我有位朋友的爸爸,他當時要選國會議員,我就開始記錄這個過程。其實當時我本來是在教書,後來我就辭去了教書的工作,開始擔任像BBC這些不同新聞台的一些牽線人。後來我發現這一些外媒都是用自己國家的角度在講我們國家的故事,所以我跟我幾個朋友,就決定想用我們緬甸自己的視角來講緬甸的故事,這就是我成立Tagu Films的緣起。我們一開始會用紀錄片,可能也是因為我們從小在緬甸看不到很多的紀錄片,我們想要記錄自己的國家,我們想要講的這些主題都是我們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賽諾康
我也要用缅甸文發言,然後再請林孫烏翻成英文。那跟林孫烏的情況相似,我其實是意外踏上紀錄片的道路。我一開始本來念的是化學,之前有個親戚跟我說,雖然紀錄片跟化學之間沒什麼關係,但後來他聽說有個職位是剪輯的工作,就因此讓我累積好幾年的剪輯經驗。後來看到有徵件計畫之後我就去申請,也因此開始接觸到了紀錄片,開始拍了一些紀錄短片和劇情短片。今年在TIDF放映的電影是《吟唱靈魂之歌》,是我在政變之後做的第一部作品。
莫妙玫札奇
其實我也是意外踏上拍電影之路。在中學的學業結束之後,我看到報紙上有個日本交流計畫的廣告,他們開放18歲以下的人申請去日本交流。我純粹只是想去日本啦,所以後來我就用我自己的Camcorder拍了一部作品。我之前其實對影像沒什麼興趣,但是這個交流的活動讓我接觸到了紀錄片當中創作跟創意的層面。之後,我們國內的瓦旦電影節開放大家申請參加,我因此接觸到了拍電影的機會,所以多年來我就慢慢的練習。2018年的時候,我創辦了3-ACT組織,我們當時也發行了電影雜誌,那也是緬甸目前唯一的電影雜誌。這本雜誌當中,介紹了緬甸的電影圈,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教育內容。我們的團體也舉辦放映會、座談會等等。我最近的作品《蟻生幻夢》是個實驗電影,歡迎各位大家來看看「緬甸短片輯#2」。
主持人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台上有兩個不同世代的電影人,但他們其實彼此都有連結,像杜篤嫻有提到說,莫妙玫札奇在17歲的時候參與了第一屆的瓦旦電影節,所以其實你們也受到電影節的啟發。這可以看到雖然跨世代,但他們彼此是有連結的,也打造了一個網絡,在不同的世代之間都有交流,我們後面也會再聊一下這一點。
我想要請你們再跟我們多介紹一下緬甸的獨立電影圈。我猜《十年緬甸》就是最新,或許也是最棒的一個典範,讓我們可以看看,在緬甸獨立電影圈裡面如何有這樣的社群和集體。請杜篤嫻先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十年緬甸》是怎麼開始的?

(瓦旦電影節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監製杜篤嫻)
杜篤嫻
《十年緬甸》的計畫其實是受到《十年泰國》啟發,我在2018年的影展看了之後,讓我開始思考自己也想要拍這樣子的片。在2021的政變之後、2022年的時候,時機也成熟了,我們總算得到了資金可以把它拍出來,就想說要怎麼去想像我們國家未來十年會是什麼風景,所以我們當時就一起討論應該要邀請誰一起來參與這個計畫。我們的製作團隊當時就是希望邀請不同的電影人,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風格,那也希望是來自不同的世代。所以我們就邀請了Tagu Films的林孫烏、TEN MEN的翁明,我們自己本身也希望可以說我們的故事。像翁明比較長,我們可能是中世代,另外當然我們也邀請了更年輕的世代,希望有不同的電影人可以一起參與。泰狄有想要補充什麼嗎?
泰狄
當時真的是很挑戰,因為我們知道十年系列其實很多國家都有拍,像我們當時就是看了《十年泰國》。2020年是我們的電影節的十週年,我們回顧了電影在緬甸的發展,慶祝了電影在緬甸的一百年,也想看看在獨立電影中,有什麼不同的做法和風格等等,當時我們的思考邏輯是如此。那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我們電影創作者的安危。因為在這樣的國家情勢中,我們必須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考量,但我們是真的很希望可以捕捉下這一刻。
杜篤嫻
我們這個計畫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在疫情之後,我們實際上能夠拍的案子不多,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幫助到不同的創作者和團隊,讓他們可以有更多收入。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好好支持整個電影產業、獨立電影的產業,尤其是在政變之後,讓他們可以發聲。
主持人
我也想要請問一下翁明跟林孫烏,你們成為《十年緬甸》這個計畫的一份子,對你們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翁明
作為一個創作者,我一直都在思考不同角色他們不同的動機、不一樣的劇情,所以泰狄跟杜篤嫻來找我拍其中一支短片,我就把一切都打開了,因為我腦中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思緒跟想法,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一些經驗,所以我當時是用這個角度切入。我常說一句話「No Trauma No Act」,你要是沒有創傷的話,可能就沒有東西可以行動或創作了。我每次看別人的作品,當然還有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我都在反思自己的作品,也會試著去看有什麼樣的創傷,要怎麼去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有機會參與《十年緬甸》的時候,我也是把這一個思想帶進來。就像泰狄剛剛所說的,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政變後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安危,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的故事跟我自己家有關、在家拍,那些拍攝不是白天跟下午,只有晚上,因為晚上是最安全的拍攝時間。
主持人
那林孫烏您身為一個製片有什麼想法?杜篤嫻、泰狄跟翁明剛剛已經講了非常多的洞見了。
林孫烏
真的很巧,杜篤嫻跟我說看了《十年泰國》之後,就在思考《十年緬甸》。其實我一開始也是,我看完《十年泰國》之後也有這樣的想法,但那時是在政變之前,所以我本來沒有覺得有什麼故事好說的,可能當時我們過得太舒適了。就像翁明說的,沒有創傷就沒有行動,這在政變之後非常明顯。整體來說,作為一個製片、一個團隊,這個政變可能讓我們有一種存在危機,我們會思考說:我們到底是誰、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我們的定位是什麼。
政變之前,在緬甸作為電影創作者,環境非常棒。尤其是你在拍紀錄片的話,真的可以出去想拍什麼就拍什麼,有很多的自由,不用擔心有什麼迫害,就去拍你的主題。但是在政變之後,大家都很想說不同的故事,可是就像泰狄剛剛說的,你不是只要擔心你的安危而已,還有鏡頭前和鏡頭後的人的安危,這些因素全部都要納入考量。那在杜篤嫻跟泰狄來問我們、開始討論《十年緬甸》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就像翁明醫師所說的,它其實就像是打開了一個氣閥,你本來很緊張、有很大的張力,它讓你把這個氣閥給打開了。有趣的是,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要寫什麼故事,但我們就是想要參與這個計畫,就說:好好好,我們答應!我們回到辦公室之後才想說,靠,我們不知道要寫什麼故事耶(笑),他們就想說趕快來想一個。後來很有趣的是,我有一個朋友寫了這個劇本叫做《親吻行動》,他有美國籍,寫了這個之後就離開了緬甸。這個腳本是非常標準的一個劇情片,後來導演跟我討論說要怎麼拍的時候,我們想要把它變成一個偽紀錄片,因為2020年是瓦旦電影節的十週年,那2023年也是我們Tagu Films的十週年,所以我們想要敘述的故事是呈現我們作為電影人的認同是什麼,我們也想要致敬紀錄片,加上我們都很喜歡《辦公室瘋雲》(The Office)這部偽紀錄片影集的形式,也知道《十年緬甸》整體來說比較沉重悲觀,所以我們想要在最後拍一部比較好笑的影片。
主持人
我也想要借用翁明的話「No Trauma No Act」,問一下其他兩位(賽諾康、莫妙玫札奇),你們並沒有參與《十年緬甸》的拍攝,參加《十年緬甸》拍攝的導演年齡大概都是40到50歲左右,兩位大概比較年輕。啊,澄清一下林孫烏今年三十九歲,還沒有四十(笑)。想問台上這兩位比較年輕的影人,兩位都經歷過緬甸2010年後短暫的民主化時期,這個時期讓大家有機會運用網絡探索外面的世界,那在政變之下,年輕的影人有受到什麼影響?

(3-ACT創辦人、《蟻生幻夢》導演莫妙玫札奇)
莫妙玫札奇
林孫烏你也年輕啦,可以回答(笑)。就像剛才說的,我29歲,在二十幾歲的年齡層,成長時期比起現在有很多的網路自由,二十幾歲可以透過網路蒐集各種資訊,當時的緬甸對世界開放,也走向民主。對我這個世代的人而言,我們並不一定認為影像要跟所謂的集體或是政治有直接的關聯。如果是上一輩電影人,他們年輕的時候也許經歷過各種危機,但我們相對比較樂觀,也有機會接觸到獨立電影節或者是外界的資訊。也因為這樣的機會,我有更多探索的經驗,去了解電影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因此我對於電影的態度,比較傾向於實驗性的做法。政變之後,軍政府奪走了我們的自由,但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還是胸懷熱情和正面的態度。我們原本以為不會有太多的機會可以放映,但年輕人不斷地拍攝,他們的作品還是不斷在各國放映。雖然政變後有受到影響,但是我們這代的年輕人還是繼續保持對電影的熱情,持續製作和拍攝。
賽諾康
政變之後大概有兩年的時間,我都很迷惘自己該做什麼,要如何繼續面對國內的處境和局勢。今年在TIDF播放的作品《吟唱靈魂之歌》,是時隔兩年後,我才決定再度開始拍片,讓我的創作生涯繼續下去。當我們繼續留在緬甸國內時,我們必須謹言慎行,說故事的時候要小心不讓自己遭殃。我在作品裡找的詞曲創作人,表面上創作的大多是情歌,但是潛藏在情歌下,其實可以用政治的角度來詮釋,他們透過情歌去討論不同的議題。我們現在必須要採取這樣的策略和形式,在限制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迂迴地討論國內的情勢,例如一些比較抽象的敘事方式,而不直接談論國內的狀況。我也看到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更常接觸補助、國際組織、國際影展等等,開始有機會也有意願接觸國外的資源來創作。
主持人
政變對緬甸國內造成很大的衝擊跟影響,對於電影圈有沒有什麼意想不到的影響或改變?尤其是在座的幾位都還留在緬甸。
泰狄
對我們來說當然有很多的困境、難處和阻礙存在,但政變之後,很多人也開始有了不同的靈感和表達方式,我們覺得身為說故事的人有更多的責任,在經驗後捕捉當下的感受、情況,並透過影像、書寫和各式各樣的媒介來表達。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這是身為創作者的責任,政變迫使我們要發揮更多創意。
林孫烏
不論多有創意,我還是不希望政變發生,但非常遺憾政變發生了、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對我的製作公司而言,政變的確迫使我們反思一開始拍電影的動機是什麼。我隨時都會提醒自己,我們並不是政治運動者,我們是說故事的人,我們想說的是跟緬甸有關的故事,這是我們不斷提醒自己的事。如果我們對於未來有小小的期盼或希望,在目前的困境下,我們更可以釐清自己為什麼一開始要拍電影,雖然在這些限制下,有些人可能覺得在緬甸還繼續拍實在很瘋狂。
主持人
杜篤嫻想補充什麼嗎?
杜篤嫻
在政變後,我們確實必須找到更有創意的方式去拍片。以前我們團隊成員非常少,政變後我們變得更明顯,要有更大的團隊。因為如果團隊很小,有時候反而比較可疑。所以我們在拍《十年緬甸》的時候,我們刻意地讓整個製作團隊更大。當然翁明剛才有說在自己的家拍,可以更安全;但我們反而是想要更明顯,在街道上人多勢眾,每個人都有找到各自的方式,讓自己可以成功地拍片。另外,身為瓦旦電影節的負責人,政變後我們就停了兩年,確實沒有一個地方讓我們可以放映。2023年,我們拿到了一個新的名字讓我們可以每兩週定期地放電影,讓我們這個社群可以存續下去。我們這個計劃持續了六個月,但只有放一些國外的片,我們也是在試水溫。在這些放映後,我們今年也決定要有一個迷你影展,當然我們也還在看確切該怎麼規劃,找一些新的方式。
主持人
各位都找到了新的方式,在危險的水域裡想辦法泳渡過去。
莫妙玫札奇
補充一下,如果可以回到2019年疫情和政變之前,我們當然會想要回去,但事實是木已成舟。雖然現在有很多的限制和悲劇,但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還是有表達我們經驗和感受的需求,同時也要注意我們的人身安全,不可以在表達自己的過程中冒險犯難。雖然疫情中很多人不幸喪生,但我們現在也找到了新的方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對於紀錄片創作者來說,更難在街上想拍什麼就拍什麼,那我們要怎麼拍片呢?你自己一個人待在家要怎麼拍?要怎麼表達你的情感?可能用比較隱晦、不直接的方式,不能很直白地表達以免激起一些反應。你的電影還是可以很政治,但不是真的在談政治,用比較抽象、實驗的方式討論我們政變後的感受。像我的作品《蟻生幻夢》和另外兩部片,都是用比較實驗的方式,也都是3-ACT這個計劃支持的,打破限制、表達自我。另外,雖然不是好事,但總之我們必須接受事實,政變某種程度讓國際看到我們緬甸的電影,像賽諾康說的,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跟國際接軌,因為國際社會開始更關注我們在緬甸做什麼。
主持人
我想問翁明,我記得在開幕的時候有聊到,你一生當中其實經歷過好幾次的政變,你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
翁明
身為一個經歷過兩次政變的人,我想要分享兩件事。首先,我覺得我跟趙德胤導演有很多有連結的地方,他也經歷了很多不同的創傷經驗。我印象很深刻,趙導說「拍片很簡單,人生才難」,人生是一個很難的體驗,我覺得這一點沒錯,拍片很簡單,經歷政變才難。真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對於這個世代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經歷真正的政變,年輕男女來到我這邊,跟我討論拍片,我都會說:「拍片不是重點,重點是你要照顧好自己,尤其是心理上要照顧好自己。你有準備好嗎?你有睡飽嗎?你有休息夠嗎?」療癒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才會說拍片其實是最簡單的部分,你要去經歷這樣的人生,這才是最難的。我自己的經驗是,會照顧自己的人,比較能夠理解自己的感受,他們的情緒更深厚,他們在拍片時才可以說更好的故事。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元素,跟大家分享。
主持人
感謝翁明醫師。各位都選擇留下來,但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藝術家都離開了緬甸,人數還越來越多,尤其是在軍政府規定要徵兵之後,讓情況變得更加嚴峻。請問各位現在還有辦法和流亡海外的緬甸影人合作或有所連結嗎?還是你們被迫要分開?海外的緬甸影人看到國內的片又有什麼看法呢?這個問題很難,我看到大家剛剛都大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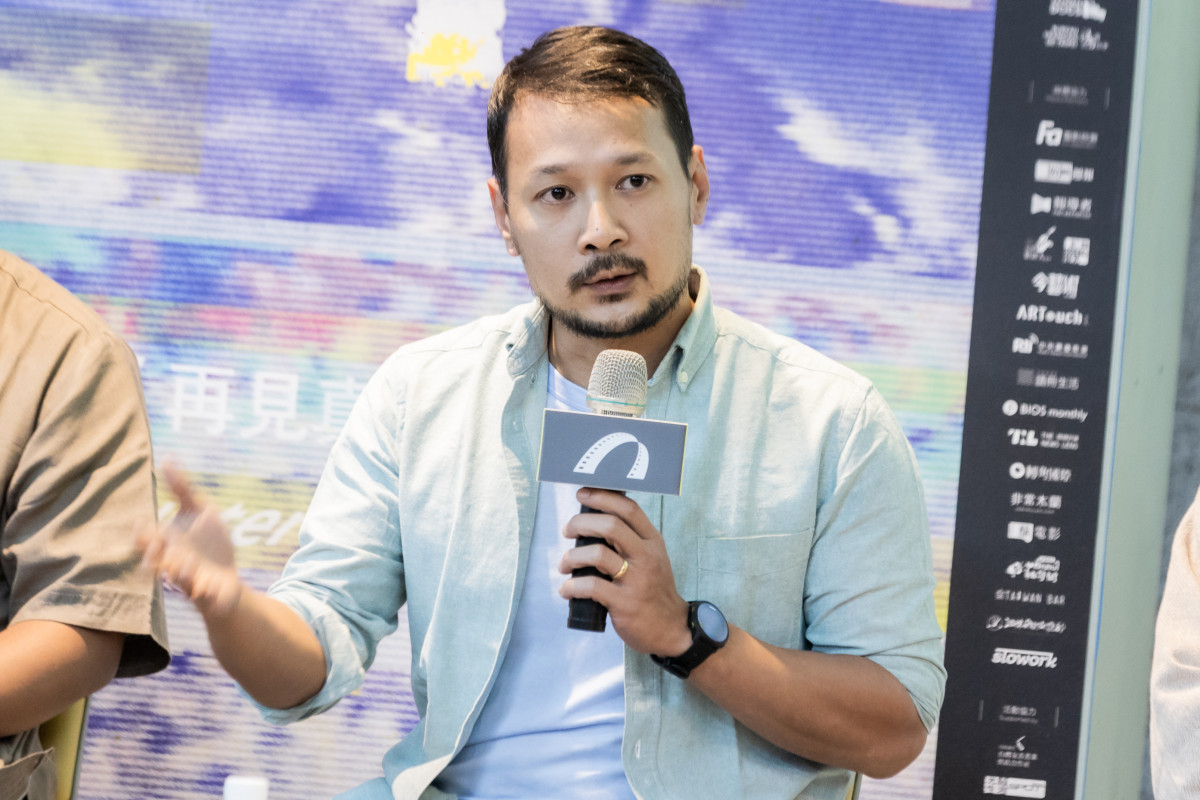
(Tagu Films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製片林孫烏)
林孫烏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政變前,獨立電影圈子非常小,社群成員都非常緊密,可是為了我們和他們的安全,我們不會真的一直保持聯絡,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彼此都互相了解,不想影響彼此的安危。他們在海外有很棒的作品,說很棒的故事,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我也非常敬佩他們的做法,但是我覺得整個脈絡非常的不同,我們經歷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徵兵法確實是有很大的影響,尤其對於我們製作團隊來說,具備技能的年輕人,尤其是男性,很多人都選擇逃到海外。像我們受訓多年、負責音效或攝影的重要成員,現在都在海外找機會。我認為他們這樣很好,他們不想參與這個衝突或被捲入其中,這當然是他們的權利,可是這對我們製作團隊設下了更多的限制,不管是要拍劇情片還是紀錄片,缺乏具備技能的年輕人真的是很令我擔憂的一件事。當然我們還是有我右邊兩位這麼年輕的電影人,但我的問題是在於我都四十歲了,我還可以持續多久?還會有什麼其他的限制?
主持人
你在作品當中也觸及了這樣的議題,賽諾康,以你的觀點,有什麼意見或想法想要分享嗎?
賽諾康
我畢竟也在被徵兵的年齡,這件事也不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如果發生就發生了。很多跟我同輩的電影人都離開緬甸了,有些人在國外繼續拍片或者從事電影相關工作,但是也有很多人放棄電影,在其他國家用其他的工作試圖謀生。
杜篤嫻
補充一下,對於這些流亡海外的同胞們,我們其實並沒有太直接的聯絡,當然我們還是會間接聽到他們的消息。4月我們剛剛完成一部劇情片,之前拍攝了一個月的時間。當時只有20幾歲的攝影師,他在快拍完時接到徵兵令,他就臨時退出了。另一位工作人員他的名字也出現在徵兵名單中,但是媽媽賄賂軍方後,他就不用上戰場。
主持人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跟當代藝術團體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他們一直都會提到徵兵這件事情或是年輕藝術家逃離緬甸的問題,這是我們一再聽到的、關於緬甸的情況,因此想問問看電影圈的情況如何,對於你們拍電影有什麼影響,或留在緬甸有什麼隱憂。各位的情況當然和年輕當代藝術家的情況也許不同,在座的大多都脫離被徵兵的年齡了。
泰狄
其實要離開緬甸也不容易,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離開緬甸。如果要離開,最平價的選項就是去泰國,但是去了泰國又怎麼辦?有些人有機會離開,有些人想離開卻無法離開,只能隨機應變,看情況再說。我們有時候也不能想太多,或是做更長遠的規劃,只能想未來兩、三個月可以怎麼辦,因為長期而言有太多的變數。但就像其他人所說,我們還是要繼續保持一定的心理素質才能夠堅持下去,這是我們現在生存的方式。
主持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持續堅定地拍電影,比如說《十年緬甸》描述友人離開緬甸到日本當移工等等。
泰狄
《十年緬甸》當中有段描述男子要離開緬甸,另外一個故事則是兩個女孩一直想要離開緬甸,都在描述能否離開、如何離開。這些都是年輕電影人思考和面臨的問題。
主持人
在泰國有不少來自緬甸的移民,他們也許透過離開緬甸尋找更美好的未來,但到了泰國還是面對很多的困境。目前在座的各位還是住在仰光嗎?比如說賽諾康他來自撣邦,但其實現在也居住在仰光。我好奇仰光以外的電影人,他們有什麼樣的資源?他們的情況如何?
賽諾康
仰光是國內的大城市,仰光以外的部分地區,所謂的解放區,他們也許還有自由拍攝的可能性,但是離開大城市,拍攝的情況更加困難,很多地方還在軍事和武裝衝突當中,風險非常高。緬甸目前的情況是你可以在大城市拍攝,或者在沒有戰火的地方相對安全。但很多情況下,大家要以匿名的方式才能夠參與。譬如說我去年拍攝過一些村莊,但今年那些村莊都已被戰火夷平,或是大家都被迫逃走了,有很多的變化。
主持人
那在國內的雜誌要怎麼發行?怎樣觸及到國內其他城市,莫妙玫札奇,你的情況又是如何?
莫妙玫札奇
雜誌方面相對沒有這麼困難,但是寄到國外的運費很高。我順便回應前面的問題,有些影人留在國內,有些影人逃離國外,我們彼此的聯繫比較少或很難聯繫。但是我認為,這兩種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影人應該要想辦法團結在一起,還是有很多的缺口存在。如果比較早離開緬甸,他們現在也許可以非常自由的表達議題,可以真實、明白地表達出來,他們的拍攝風格、導演風格就會傾向那個方向。在國內影人所拍攝的作品,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相對中性,因為我們想要盡量地淡化,或者不那麼直接地觸及,我們因為安全問題和個人安危,不能這麼直接地發聲。這些在海外的緬甸影人,看待我們的方式或許會有所不同。他們流亡海外一段時間後,敘事風格也會改變。政變一年後,我們還留在國內,希望維持這樣的社群和網絡,希望大家還有更多機會可以繼續創作。但在徵兵法公佈後,我覺得非常令人心痛,確實有很多年輕人因此不得不離開緬甸。當然對男性直接的衝擊比較大,但是女性也有受到不同的衝擊。現在才離開緬甸的人,相對兩三年前離開緬甸的人,他們的處境和動機又不太相同,這也造成不同時期離開緬甸的人,他們的態度都有所不同。
主持人
我知道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再次感謝剛剛各位願意回答。剛才有提到說打造一個獨立電影人的社群,打造自己的網絡,甚至是自己的機構。大家自我介紹時也有提到自己的團隊,是不是可以再請各位再介紹一下電影學校、工作坊,或是電影節,你們都是怎麼交流跟激蕩,傳遞這樣的電影教育?

(瓦旦電影節共同創辦人、《十年緬甸》導演/監製泰狄)
泰狄
像賽諾康參與的仰光電影學校,到現在還是有舉辦很多的工作坊,還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還是可以持續在仰光做紀錄片工作坊。仰光以外就越來越難存活下去,尤其是比較小的村莊,因為有很多的內戰和政變等等。對於我們來說,我會跟不同的組織一起合作,辦一些線上的工作坊,針對清邁等等邊境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沒辦法露臉或呈現真實姓名,所以我們就用線上的方式,用Zoom一起討論。我們的放映也希望可以趕快重新開始,但還是要等等看,看我們可以做什麼,因為讓年輕人聚在一起已經有點危險了,我們真的都不知道有誰會是政府的線人。我們現在會重新開始迷你電影節、迷你影展,我們會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像是一些文化藝術中心。在2005、2006年剛開始拍紀錄片的時候,我們也是找到這些比較安全的地方,文化藝術中心可能會再次變成年輕人很重要的據點,可以聚在一起討論,讓他們的紀錄片可以重新蓬勃地發展起來。
莫妙玫札奇
其實大部分跟年輕人有關的社群,政變之後還是希望可以維持這樣的精神,過去這三年都是如此,雖然我們無法做很大型的活動,但還是會有一些小聚會、小活動。可是在徵兵法公佈後,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衝擊,因為這個法令的頒布讓一切都靜止了。文化藝術就是要讓年輕人在一起,沒有年輕人你還能怎麼做?還能怎麼辦?我覺得現在真的很困難,我們很難繼續往前走。疫情也讓我們透過不同的角度開始思考,有很多年輕人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維持我們的網絡,可能是線上的方式,或是到不同的國家快閃放映等等,就是要重新想辦法跟年輕人連結,我也還在思考,持續腦力激蕩。
翁明
過往有不同機構可以培訓年輕的電影人,像是電影學校、藝術大學,你真的可以看到當時的年輕人到處漂泊或找我說想要學電影。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逃到國外了,有些人還會跟我聯絡說,你當時在教我們的時候,我沒有仔細聽、好好聽,但我現在真的很想拍電影。另外一個我還有執行的計劃,就是讓有心理和精神問題的人做藝術,那當然有不同的做法。一個是要用很正式的方式和觀點教大家學術理論;但面對精神障礙者,就是叫他們做就對了。所以我現在覺得,藝術就是去做就對了。無論用什麼方法,你就是去執行就對了。我的建議一直以來都是,不管你在美國或某個森林裡,你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個態度說,我想要做藝術,我想要去做點什麼。很多時候你腦中會有很多限制,但你就是要把它丟掉。
我有看一些台灣的電影,有些比較早期的影片,他們真的沒有自我設限,他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要表達什麼就表達什麼。我在緬甸的電影中也有看到,我們就是用我們知道的方式去拍片,用我們手邊有的資源拍。我自己是老一代,能給年輕人的就是鼓勵年輕人去做,若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能可以回來用比較傳統的方式去學習。我當然可以教他們一些傳統的學術理論,但我覺得還是要踏出第一步,鼓勵大家探索不同的方式。至少這是我自己試著要打造的一個電影社群。
林孫烏
我前面有提到我們Tagu Films有存在危機,也讓我們重新定位想做的事。尤其是在很多限制下,我很喜歡剛剛翁明說的,自己去找可以敘述故事的方式。我很高興我跟賽諾康一起合作過,他是撣族的人,我們也找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一起做工作坊。我們Tagu Films的共同創辦人拉明烏(他在TIDF也有兩部片)跟賽諾康和我都是一起合作,試著教撣族年輕人拍電影,我們有足夠的設備教他們怎麼用攝影機、處理音效。去年我們製作了四部紀錄短片,我們自己也非常意外。
這裡也講一下背景脈絡,我們Tagu Films創辦人正好是來自四個不同的族裔,包含撣族、克欽族、孟族,我自己本身則是緬族。我們一直都相信緬甸大部分的故事使用我們緬甸語(Burma)這個語言,但很多時候你沒有辦法完全代表所有人,因為畢竟我們有超過一百多個不同的族裔,我們有讓少數族裔用自己語言說故事的夢想。另外,在這兩年,後製是比較困難的部分,可能要花幾年的時間才可以學會剪輯,可是對我來說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因為可以賦予他們權利,用少數族裔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剪輯有時候最久,因為需要從一個語言翻譯成另一個語言,我很多時候還要翻譯成英文、加字幕。這是我們在安全的範圍內,一直想要做的事。
但我也想要特別指出,即便是在政變之前,拍電影就已經很困難了,你要拍很多的短片,拍完才可以認識更多的人脈,一起來做共同製作才有資金,這可能要花好幾年去累積。過往對我們製作人來說,我都會說來跟我們一起學習,我們可以幫你製作短片,或許你就可以去一些電影節,做共同製作,這是我們以往鼓勵年輕人踏上的旅程。過去十年、政變前,真的有很多很有才華的電影人跟我們合作,可是政變後,我沒有辦法說服年輕人一起來拍片。我記得有個年輕人,他在考慮要拍片還是逃到國外,他問我現在拍片情況如何,我跟他說拍一些紀錄短片參加電影節。那他說,會有錢嗎?我說不會有薪水,入選、得獎後或許可以加入共同製作。他說,那要花幾年呢?我說大概四、五年。他就說,老兄,我有肚子耶,我要餵飽我的肚子。你沒有肚子嗎?你是怎麼餵飽自己的?
尤其現在政治和經濟情勢又這麼糟,真的很難去說沒關係,五年之後你可能會是下一個大導演。現在有太多障礙,我真的很難去說服他們不會有事。當他們問前景如何時,我很難回答他們,現在還是會想盡各種辦法從事電影工作,但的確有很多實際的層面,畢竟大家都要找飯吃嘛,光是拍片,未必能達到養家糊口的收入。
主持人
謝謝您的回應。剛才有提到緬甸不同族裔之間的合作,跨族裔合作是新的現象嗎?
林孫烏
我不覺得是完全新的概念了,畢竟在電影學校我們有開放少數族裔年輕人來報考。我自己的夢想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工作坊的模組,讓其他族裔能根據這個模組,自己辦工作坊。首先我得要去說服合作夥伴讓他們願意做這件事,因為我是緬族人,我很難進入少數族裔做工作坊,因為緬族是多數族裔,我的身份去教他們做事情的話,可能又是一種種族霸凌,所以我希望當地族群內部自己建立起工作坊,否則會是殖民主義的情況,這不是我樂見的。
泰狄
現在比較困難。過去在不同地區的小型放映,比如說我們會到撣邦、欽邦地區跟當地的電影人合作舉辦,但現在比較困難了,一方面是安全的考量,國內族裔間的關係也非常複雜。2020年疫情爆發後,我們轉向線上舉辦,幸虧有網路,全國各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當時線上有15萬人次收看。政變前是線上、線下混合型的影展,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作品,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舉辦。
主持人
我也想問賽諾康,你在《吟唱靈魂之歌》映後座談有提到,你不是用「剪輯」,而是「譜寫」(compose)這個詞彙來構成作品,我很喜歡你在想像畫面或是建構影像的方式,不是用剪輯的方式來想像作品的形成。

(《吟唱靈魂之歌》導演賽諾康)
賽諾康
我會用「譜寫」是我之前就讀仰光電影學校時,在電影理論裡學到的,在不同的課程中,想像創作過程中比較適合的詞彙。我過去並沒有到海外學習電影的經驗,都是仰光電影學校教給我的,包含電影拍攝的美感和技術等等。至於用「譜寫」來取代「剪輯」,是因為這類似我潛意識裡對於剪輯和創作的看法,電影比較像時間流動的過程,這個時間流當中有些片段需要某些畫面,我就把它放進結構當中。
幸好仰光電影學校還在運作,而且有不同族裔的學生在就讀。有些少數族裔的學生到了大城市來讀書,很遺憾的是,他們的村莊被轟炸、被軍隊入侵等等,使他們的情緒一直非常低落,但他們還是繼續上課,試圖在有限的空間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電影。現在做短片或紀錄片,相對而言資源需求比較低,劇情片的成本或資源需求可能更高了。
主持人
感謝各位今天跟我們分享很多不同的想法。我們的座談告一段落,現在開放給現場觀眾提問。
Q1
感謝各位,我來自香港,我也是紀錄片創作者。我好奇仰光電影學校的課程,課程裡面有提供什麼內容?比如說緬甸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議題,或是介紹東南亞、中國等其他國家的情況嗎?當地學生對課程設計有什麼看法?
主持人
這一題針對仰光電影學校,可能要問賽諾康或翁明,因為翁明也有在教書。
賽諾康
仰光電影學校課程是非常務實的,基本上是三年的學程。針對初學者,他們會教你基本的拍片技術,還會有一些學生實作,他們會請學生拍攝和剪輯不同的素材。繼續往上讀可能會有一些資金去拍更廣泛的,比如說15分鐘的紀錄片,另一部分是怎麼調光、音效、後製等等。另外,招收學生的比例主要是6男6女,配額有一部分是保留給不同的少數族裔。導師可能來自國外,教他們做後製,讓他們跟不同的影展有所連結,去不同影展時,其實就能鼓勵或啟發學生
林孫烏
我可以順便工商一下我的工作坊嗎?我們的工作坊和學校比較不一樣,我們沒有一個組織機構,是非常草根型的一群拍片人。我們會播放可以取得的片,所以我們會去找杜篤嫻和泰狄,說我們想要放這些片,你們有片源嗎,我保證只有學生,不會跟任何人分享。或是問翁明有沒有時間來幫我講個課等等。很多是朋友之間或是東南亞電影圈的朋友,我會去問有沒有影片連結,能不能借我用。我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壓力很大,因為國內就剩下他一個人,我現在在台灣享受美好人生,有點內疚(笑),但我還是會回去幫忙啦。我知道在這個場合工商有點無恥,但如果各位願意來參與或幫忙,都歡迎來跟我聯絡(笑)。

翁明
身為講師,我們會受到歐洲、西歐的影響,但在教學中我會刻意的介紹東方的電影。如果學生要認識歐洲的導演,也應該要認識亞洲的導演,我都會想辦法去平衡。我會介紹一些東方的片、小津安二郎等等,這些導演的作品是永恆的經典。我給他們看了之後,他們說之前看了很想睡覺,你可不可以再給我看一次?我都會說,你們下次回來,我會再跟你們介紹。
Q2
幾年前我看到一個電影合輯,講到不同的亞洲國家和環保議題。在政變之後,是不是更難做跨國的合作,還是說政變後國際合製變得更加的重要?
莫妙玫札奇
剛剛賽諾康也有提到,幾年前我們開始更能夠站上國際舞台,有更多國際的關注。我個人的經驗是去年有跟日本的計劃合作過,但不是製作電影,而是工作坊。另外我也很同意現在有很多緬甸人四散,雖然我來自比較敘事型的電影背景,但我不會幫自己貼標籤,我就是拍電影來表達自己,不管用什麼形式或方式,其實就是看我想要說什麼故事,不去管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政變後,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沒有很多資源,自己拍片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不需要等很多資金或很大的製作。舉例來說,你在泰國想要拍片,你要怎麼去模仿緬甸的氛圍?所以你現在要拍劇情片很難。你要怎麼找經費、找到製作團隊?但紀錄片或相對抽象的片,我覺得反而更加容易。相信其他人也可以分享他們的經驗,但我覺得政變後,我們也得到更多機會,像是去年也有泰國的組織專注在宣傳東南亞的電影。有很多新興的創作者他們本來是拍短片,我們就一起去申請曼谷的計劃,是一個讓年輕電影人參與的國際計劃,以後可能就有更多國際合製的機會。當然如果是歐洲的合製,目標就更高、更遠了。相信其他講者也有國際合作的經驗。
主持人
賽諾康也想要分享你的想法嗎?
賽諾康
我們的《湄公河2030》(Mekong 2030,2020)是當時更有自由、想要表達什麼都可以的時候進行的,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我只能這樣講。舉例來說,像是對話的選擇,現在你仔細思考的話,在這個脈絡下會有很多的爭議。這種國際合製或是合作,我覺得剛剛的講者已經回答很多了,但是問題還是存在,到底是多了很多機會,還是機會變少,其實大家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Q3
我本身過去兩年也有在拍電影,我們有看到很多共同合製。我想請問,如果把這些電影帶回一開始拍攝的地點,當地的社群會有什麼樣的回應嗎?
林孫烏
我們的工作坊當然之後有作品完成的話,都會在當地放映,一般來說迴響都非常正面。在比較偏遠的地區,他們往往都會認為電影離他們很遠、拍電影的人離他們非常遙遠。我們在工作坊的時候,都會好奇問他們為什麼要拍電影、拍電影的動機是什麼。我們在做放映時,會希望透過放映,說服當地民眾拍自己的故事,讓自己的作品出現在銀幕上面,這是其中一項動機。另一方面也是用更務實的方式,說服當地的地方政府,讓民眾有機會、有能力、有空間帶著攝影機在大街小巷拍攝。
賽諾康
實際上,我們舉辦工作坊的時候,最大的困難是要說服他們拍攝紀錄片有其意義和價值存在。很多人以為拿攝影機應該拍表演或音樂錄音帶等等,光是要說服地方民眾、耆老、當地官員讓我們做紀錄片工作坊,其實都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說服參加的民眾,自己拿攝影機拍紀錄片、自己發聲是有意義和價值存在的,請大家把握機會嘗試。實際上舉辦活動的過程非常順利,我們會教他們怎麼用攝影機、怎麼運鏡等等。他們拍攝的議題也涵蓋非常多的內容,包含政治、歧視、性別等等,這些都未必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議題,但都是他們自己在生活中體驗到、好奇、有想法的議題。另外,他們拍攝的情況的確就是現實,能夠反映出當地的局勢,我們也把這些作品帶到當地放映、讓在地民眾看到。
主持人
感謝林孫烏今天幫我們做緬語和英語的翻譯,很遺憾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必須要在這邊告一段落。結束之前,杜篤嫻和泰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泰狄
我開始對紀錄片感興趣的時候,大概是2005、2006年的時候,當時是軍政府統治時期。後來有機會看到《氣旋納吉斯:當時間停止呼吸》……啊已經十五年前了,有點久(笑)。我在今天討論的過程中,回想自己當初為什麼會對紀錄片產生興趣,是因為紀錄片裡面傳遞的真實非常重要,我在紀錄片中找到共鳴。在過去軍政府統治下,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實的情況,很多的事實都被掩蓋,所以當時有機會看到紀錄片、看到其中的真實時,我產生了很多的想法和觸動我的經驗。現在緬甸的情況又大不相同,我相信未來紀錄片會扮演不同的角色,即使在政變之後,我認為了解真實、接觸真實,對我們來說又有了不同的意義和重要的意涵。
主持人
感謝您最後的結語,即便發生了這麼劇烈的事件和變化,還是不會失去希望,繼續往前進。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