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映後座談
時間:05.12(SUN)13:10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一廳
主持人:楊子暄
出席影人:導演 許家維
攝影:李僑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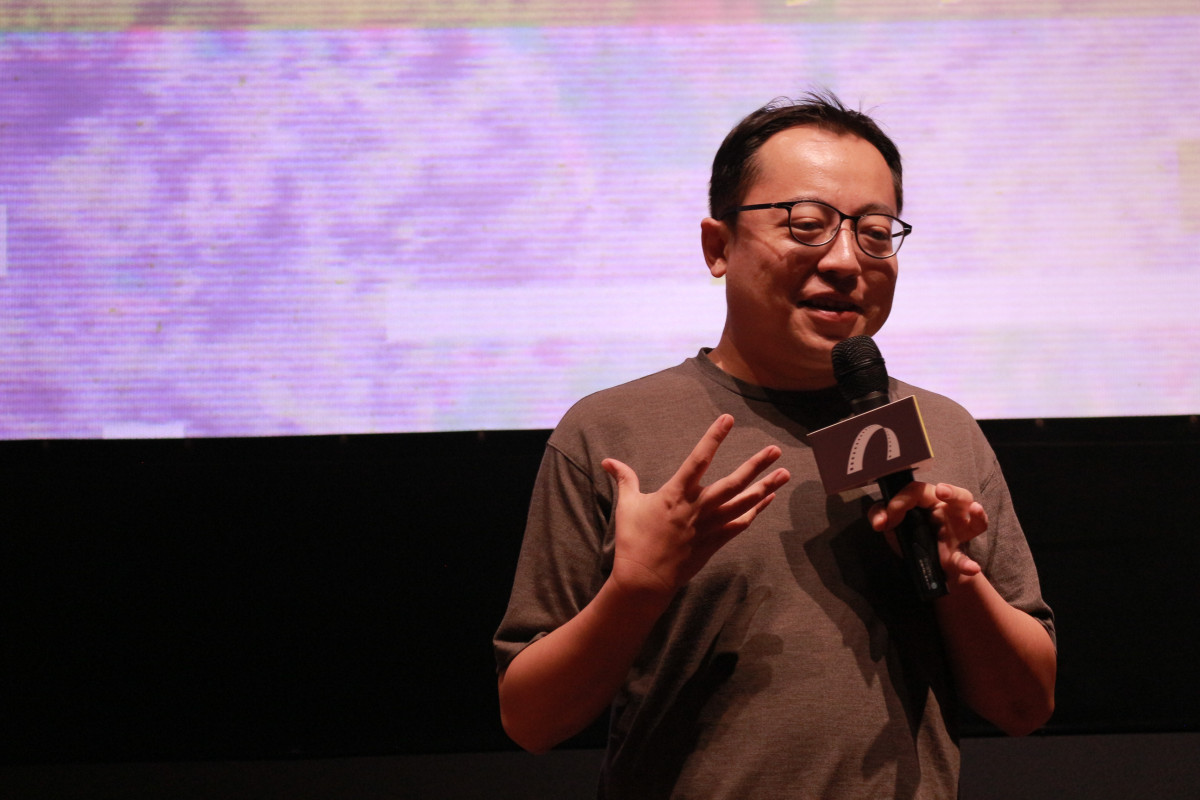
主持人
這是《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世界首映,很高興大家來,先邀請導演許家維。
導演
因為我這部電影其實很後設,所以我猜很多我需要說明的東西也在裡面,所以應該大家會很了解。也許我可以講一些緣起。因為我的背景是當代藝術的錄像創作,大部分發表平台在美術館。在2008年我曾經做過一個錄像作品叫《和平島故事》,拍攝地點是現在和平島造船廠,當時這個作品,其實我比較關注是日治時代歷史跟造船廠的關係,然後大概在2014年,我看到新聞,有中研院考古學家正在針對那個地方做研究,是針對荷西時期,讓我覺得很好奇,我就一直想要再回去,那個我2008年做的作品,原來底下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裡。直到2018年,公視有機會讓我提案做紀錄片創作,我就說想做考古主題。但你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很難界定,考古的紀錄片,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包含我自己創作的經歷跟考古學家的經歷,還有聲響創作的發想,其實有很多不同路線在這裡面交織,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分類、界定,你們到底看了什麼東西,大家如果有問題,就可以提出來討論。
主持人
我自己也想要先問一下,像導演提到裡面有非常多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交織,例如:影像、音樂、考古。你是怎麼思考這三個之間的關係?如何組織?
導演
這創作過程都是一步步慢慢發展出來。我倒著講,你們剛剛看到最後的credit list,其實在很多不同地方拍攝,在國外的時候,常常只有我一個人是台灣人。我的狀態很像,這個工作過程像是臨時工作社群,我常常是團隊裡面最不懂的那個人,因為所有人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考古學家有專業,音樂家有專業,或是文史研究者也有其專業,最不懂的就是我。所以我有點像是觀眾,經歷了這些後慢慢把這些組織起來,我有點像是代替觀眾進行這趟旅程。你也可以感受到我的影像組織,比較不是線性的敘事,而是在這裡面有不同領域互相打破、交織,跟各種線索互相連結。這個敘事比較像是互相有關聯的網狀關係,這是我覺得一個啟發,這也像是我們當代人怎麼去想像事情,這也像我們當代的的思考方式,我們用這樣的邏輯,而不是起承轉合的故事在想事情。
主持人
那可以細問,實際上要怎麼跟不同領域的人工作 ? 可以講講這個工作方法,你要怎麼傳達你想創作什麼樣的藝術?
導演
這個很難耶。因為我就是最不懂的人,我在不同領域專家學者面前,就是無知的人,有點像是學習吧,所以我並不是有很明確的分鏡,或是很明確一開始就要拍什麼,這創作過程很像一個舞台,讓這些不同角色在裡面開始去產生一些關係跟意義。而不是大家依著某一個腳本,或既定的目標在裡面演什麼,或發生什麼事。而是在這個舞台,讓這些人碰撞,自然他們之間會產生一個事情,所以我覺得我的拍片方式像是設定一個舞台,讓這些事情在裡面發生。我講的可能不是電影語言,我的創作像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因為我都是跟這些不同人合作,所以很多都是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我是在這過程裡面才發現,所以創作就是一個發現的過程。
Q1
我主要有兩個疑問。我們在電影裡看到導演跟剪接師的對話,那我們通常在電影裡很少看到這個非常後設的視角,想問導演為什麼想要把這段剪進影片裡面?第二個疑問,主要針對影片中歷史的部分,裡面有講到台灣的鹿皮貿易,其實這也是跟柬埔寨及荷蘭之間在金邊河上的一場戰爭有關,影片有講到是,柬埔寨封鎖金邊,所以荷蘭去攻打他們。那當時柬埔寨為什麼想要封鎖這個河,讓荷蘭人沒有辦法進去?
導演
這兩個問題有關,我可以連在一起講。其實你可以看到有那個剪接室的畫面,我其實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越來越體會。雖然有很多考古畫面,但裡面其實沒有特別跟你講太多,比如這個修道院有什麼故事,這個和平島有什麼故事。我覺得我有興趣的是他們工作過程本身,而不是過程產出的這些,後來可能被其他人傳頌的這種背後的歷史故事。這樣的興趣也反映在,像剛剛說的會出現剪接室,或有些影像會揭露空拍機,或是看到我自己在裡面。我在這裡面其實想關注的是「工作過程」這件事。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事,其實都沒有人根本真的知道,因為我們都是用想的,所以他跟我們的當代技術有關,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技術來想像事情呢?古時候,薩滿可能是用它的儀式,我們今天有自己的技術來想像。所以我的這個影片有點像,我想呈現的是,當代怎麼想像遙遠的時空的技術,這是第一點。所以剪接室的部分就是這樣,我作為這部片的導演,我想把我的工作過程也呈現出來。那剛剛講到柬埔寨,其實裡面沒有真的解釋很多細節,我沒有真的進到每一個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細節。但還是可以額外補充,因為我是看了一本柬埔寨的一本,在講柬荷戰爭的書,其中描述到荷蘭東印度公司船艦進來這個湄公河,柬埔寨國王就是選擇把河道堵住,把這個艦隊封在裡面,從陸面不斷地攻擊。但當時也有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跟荷蘭人為什麼在競爭日本的市場,中國也扯進來,中國進來幫助柬埔寨走私等等。很複雜,但因為這不是裡面的重點,所以就沒有描述。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畫面,不是要呈現一個完全歷史的紀錄片,或是再現,裡面的很多影像都是當代,但這些當代的場景跟元素,可能都跟某一些時空有關聯。
Q2
我有兩個問題,導演的考古紀錄片蠻非典型,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的一些考古紀錄片,想知道導演是怎麼說服清大合作,因為我剛剛看到甚至是在考古現場有做音樂展現,這部分會不會有聲音是覺得要考慮文物保護。想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這樣一種新的合作方式? 像導演在影片裡講到,原本無聲的東西,要怎麼有聲去呈現?第二個問題是,導演有沒有其他遺址,也有這種拍攝計畫?
導演
剛剛這個問題滿重要,就是東西怎麼做出來的。其實現場有清大考古學家在現場看。我可以講一下背後的過程,我前面講到因為有興趣,所以跟公視提案有這樣的拍攝想法。然後我就開始看這些考古學家什麼時候要做研究,什麼時候會在現場,我其實一開始寫email都沒有回覆,想盡各種方法想要聯絡,但都沒有下文。後來想到一個方法,好像是基隆市文化局的FB,他們要辦一個里民說明會,因為考古學家要在這裡進行很長時間的考古挖掘,就要跟里民說明。我就想,之前聯絡都沒有用,我就直接殺去里民大會現場。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去和平島,遞名片說明我想要拍攝這樣的紀錄片。很幸運,因為其中一位計畫主持人謝艾倫老師,他對這個奇怪的事情,想法滿開放的。所以後來就邀請他來看我其他展覽,他可能也可以體會到我是在幹嘛,陸陸續續,我也有不同的展覽計畫,也有邀請他到美術館來做考古的分享或對談,我覺得應該有讓他越來越融入圈子。
還有一件事可能也是剛好搭上,就是現在考古學界,越來越在意公眾考古,就是考古怎麼讓民眾更認識。因為民眾可能對考古有不同想像或誤解,覺得是研究恐龍或什麼。所以這種不同類型創作,像是增加更多不同介面。就是我們可以讓平常在看藝術展覽、看電影的人,意外地碰到了一些考古的東西。當然還有另外一點,我們的確已經有一些考古相關的紀錄片,好像也不用做重複的事情。而且重複的事情又是在同樣的圈圈,同樣的受眾,那既然這樣,好像往不同領域的結合,更能夠開啟不同的介面。針對第二題,目前的確是有新計劃在進行,接下來想針對澎湖周邊,有關水下考古的沈船遺址拍攝。這個計畫也會在明年六月,在北美館呈現。

Q3
導演在鳳甲美術館的展,也是會透過聲響表演的形式去回顧歷史。可不可以談談聲響還有表演創作這部分,跟歷史之間的關係?這次選擇作曲家是香港作曲家,有什麼考量?
導演
第一題是跟表演跟聲響有關,有兩個層面。在這部片比較不明顯,但剛剛有提到鳳甲的一個展覽,大家有空也可以去鳳甲美術館看展,到6/30。我有很多作品是跟傳統表演藝術合作,比如說能劇、布袋戲,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有時候我們想處理的東西,在遙遠的時空,這些都已經不存在我們生活日常裡,有時候我們卻可以在傳統表演藝術找到。因為傳統表演藝術有一個格式,把某一些元素封存在裡面。所以透過這種方式,他有點像是你可以開始跟遙遠時空的元素做一個對話。但同時有利有弊,因為這種獨特能封存幾百年的方式,相對的也會形成跟當代日常生活的一個距離。我的創作常常想要把它帶到日常的空間。比如說帶到一個現代的工廠,這是一個原因,所以我的創作很多都跟這些表演藝術有關。
第二個疑問,雖然這部片沒有達到我的理想,但我有一部分也是從這個角度去想,聲音是不用讀很多東西就可以聽的,它是很感官的。我們面對這些聲音的材料,特別是我們去處理這種背後有複雜的資料或文本的時候,你可以不用搞懂很多資訊,只要去聆聽就好。我覺得用這種感官,這種方式面對複雜文本,好像是個有趣的方法,不用太快陷入好像要讀什麼歷史課本。選擇香港作曲家許德章,其實沒有跟作品有關的原因,只是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在台藝大教書,他的背景剛好跟我有點相似。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在法國Le Fresnoy ,共兩年的時間。Le Fresnoy 是一個以電影跟當代藝術跨領域的機構為主,那時候許德章在IRCAM。所以其實有點像是聲響領域跟電影錄像領域,我們當時在法國,算是同樣一個方向在進行,我們有很多概念其實很相似,就這樣合作。像我剛剛講到那個網絡化、舞台的關係,許德章在處理聲響也是這樣思考,你們可以看他如何讓這些元素在聲音的場景去交織,而不是很明確這個曲子就怎麼樣的一種方法。
Q4
這邊是自強工程,很榮幸有機會跟張教授這邊合作,我們有一些公司的成果展現在這個紀錄片。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紀錄片提到,用當代技術還原以前的環境,導演這邊也提到用聲響讓接近400年前的聖堂去回復它以前的感覺。那我想請教的是說,這次西班牙學者講到測繪技術,去讓考古能夠更多元化,那可以請導演談談未來在澎湖水下這個環境,有什麼樣的計畫?
導演
順便幫自強工程工商一下,你們剛剛可以看到其中一個片段,一開始從很近距離地看到人骨的牙齒,然後慢慢的最後到一個有點像google的整個考古遺址的物件。他們跟考古學家合作,用了很多種不同的掃描技術,讓它能夠完全地被掃描下來。你可以從很細微的,一直到比較宏觀視野來看場景。這件事好像也可以在考古會有很多新的發現,但我不是專業,這部分我不能自己詮釋太多。但我剛剛講的這個,水下考古在澎湖,其實也有點類似的結構,一方面我們會拍考古學家在水下的工作過程。另外我們也會依據這些沈船背後的文史資料去作聲音的發想。比如說沈船那個時代的音樂,或說這個船上的物件,也會做水下這些深井的採集。比如說海底下深井,目前這些沈船的上生物等等,這些我們都是可以去收音。然後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用這些元素去做一個特製的樂器,我們會到水底下,讓表演者潛水下去用這個特製樂器演奏。另外還有一部分,因為北美館會有VR,所以也會用大量動畫有關的內容,把這些全部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