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島影#3」映後座談
時間:05.12 SUN 12:30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小影格
主持人:李柏緯
出席者:《輻射將至》導演 周美玲、《浮球》導演 李志薔
攝影:王文玨

(左起:《輻射將至》導演周美玲、《浮球》導演李志薔)
主持人
非常感謝各位來到國家影視聽中心觀賞「流離島影#3」的放映。 這次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兩位創作者到現場,分別是剛剛看到的《輻射將至》導演周美玲,及《浮球》的導演李志薔導演,我們請兩位上台。
因為很久沒有看到這些作品,想先請周導跟我們分享一下,身為企畫發起人,是怎麼樣把這麼多導演抓在一起,然後同時又要身兼創作,在這部分有沒有什麼角色上的拉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周美玲
先謝謝大家來看這個24年前完成的片子,現場有人25歲以下嗎?(有觀眾舉手)哎呀……(倒抽一口氣然後笑)(李志薔:都還沒有出生。)對啊,你們那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在20幾年前,我們1999年開始做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們最緊密的關係是酒友。為什麼會開始啟動這個計畫,是因為那時我20幾歲,剛剛有舉手的你們一定都了解,那個年紀就是開始在探索這個世界,包括這個世界的內容,也包括探索創作、探索酒精是什麼,探索種種的。
我們是創作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那時候我好像住師大路那邊,我們常常聚會的地方是一個叫「地下社會」的酒吧,現在好像已經倒了,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整個計劃就是從「地下社會」這個酒吧開始。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還有《誰來釣魚®?》的導演陳芯宜,這幾個人在「地下社會」喝酒的時候,大家就互相聊:欸你最近有什麼創作計畫?我們20幾歲的孩子,其實再有什麼計畫,我們也沒有能耐、沒有資金可以完成,可是我們手邊都有Bolex攝影機,就是16mm的電影攝影機, 或者是DV攝影機……就是影像創作工具我們是有的,還有一顆大腦,我們有無限的夢想,和一顆神經病的心。
我們在聊創作計畫的時候,會聊手邊有什麼樣的資源、什麼樣的創作工具可以拿來創作,然後有什麼計畫。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先聊到,想要用5年的時間走遍所有的離島,用自己手邊的攝影小機器去拍一些東西回來,然後大家喝了酒就開始回應說:那我也要分一個島,台灣周圍有12組離島,我們也來分一些島啊!我們大家一起去啊,就一起玩的這種概念。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fun,很有意思的概念。
可是接下來我們就會繼續深入地討論什麼叫做紀錄片、什麼叫做創作、什麼叫做真實……等等的所有的這些概念,我們在喝酒聊創作的過程中,會不斷不斷地激盪跟討論,然後最後共同孵育出這樣子的一個計畫。我們喝酒的夥伴也許只有7、8個,就再湊足12個人,最後我寫了一個企畫案去公共電視提案,替大家爭取到500萬的資金,我們就分配給每個導演50萬,還缺兩部片子就由我自己這邊吸收、再另外去籌措,大家相約用一年的時間,一年之後大家都必須交出一個離島的短片,然後我們會在這個短片計畫裡挑戰什麼叫做紀錄片。
所有現實的素材都只不過是你創作的素材,我們的創作是一個針孔攝影機,意思是什麼?我們要有觀點,我們希望所有創作者提出自己主觀的觀點,我們不要假裝客觀的那種、自以為是客觀的報導,我們不要這樣的東西。我們試著看可以在觀點、美學上可以再做一些嘗試跟突破,那這是我們這群人共同有的共識,然後我們就這麼去做了,大致上是這樣。
不過我自己覺得對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滿意,因為在那一年裡整個投入到總製作人的身分上,真的沒辦法進一步創作,所以有了「流離島影」的教訓之後,我就再也不當製作人了,就都全心做創作。但如果時間再重回一次,我覺得再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我還是要以製作人身分為主,因為我們的確把它操作得非常好玩,也因為很大膽的操作,爭取到了一些資源挹注。最後在公共電視台播放的時候,引起了不少的批判跟迴響,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嗎?罵聲連連,但我們其實在創作路上是得到非常多啟發的。
主持人
好,謝謝周導的分享,非常地充實。這個部分想要延續到李導這邊,剛剛有提到播出之後罵聲連連,那你再回首這段創作到現在20幾年了,看到這個片子再有機會跟一些老朋友、年輕朋友相見,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或是對於這次放映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李志薔
剛剛說了那是一個熱血澎湃、充滿了熱情跟浪漫的一個時代,雖然我們取得的資金是從公共電視來的,但是公共電視非常尊重創作。當初美玲提案的時候,我跟她一起去公視,然後他們的節目部經理、紀錄片經理告訴我們說,他可以容許我們大膽地去做創作。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挑戰那個時候對紀錄片的一些看法,其中我講幾個比較有趣的,當然第一個跟釣魚台有關的,因為它涉及到中台日的一些很敏感的政治神經。那公共電視在平台上,尤其你想像24年前它還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國家的頻道,當然會有些敏感。其中我不曉得,我建議你們去看看沈可尚的北方三島,他那個北方三島從頭到尾沒有聲音,就只有影像但沒有聲音,所謂沒有聲音可能是連環境音、旁白什麼都沒有,他把它取名叫做《噤聲三角》,原因就是他覺得那個地方是人不應該去的地方,只有動物跟植物的存在,所以他用一個植物誌或博物誌的角度去看。
公共電視收到這個影片之後,他們本來鼓勵我們可以大刀闊斧去創作,但是他們突然也遇到困難了,就說會不會觀眾哪一天轉到公視、正在播的時候,發現原來公視這一台聲音壞掉了。聲音沒有嘛,轉到其他台都有聲音,但是轉到公視就沒聲音,所以他們非常苦惱這件事情,最後還請沈可尚在節目開頭的時候錄了一段說明,就是導演現身說法「為什麼以下你看到的影片它不是故障,而是故意沒有聲音」,諸如此類的、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們後來全部的作品就像今天一樣,我們把它翻拷成35mm的底片在戲院放映,也在紀錄片界掀起了很多風潮,當然有好的聲音、也有不好的聲音,但是至少一直到這一、二十年……
周美玲
不好的聲音比較多,因為史上從來沒有哪個電影創作者這樣折騰觀眾,你知道怎麼折騰嗎?我們12部短片加起來是288分鐘,中間沒有中場休息,在戲院裡面就是從頭放到尾,你受得了嗎?然後這紀錄片又很枯燥,裡面可能還有默片。後來可尚的那部影片,他做了另一個版本是整個交響樂……交響樂貫穿整個影片的版本。我猜我們這裡放的是交響樂版本。
主持人
這個我們可以等到時候場次就揭曉,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周美玲
我記得在電影院放映的時候,12位導演輪流擺攤,在戲院放映外面擺了一些離島帶回來的特產, 12個人很好輪嘛,每個人輪個2個小時,觀眾在裡面看煩了、看膩了、有疑問了、想要訐譙的,就走到放映廳外面去跟導演辯論,然後導演會請他吃一些特產再回來繼續看片。我姊姊還特地去捧我們的場,然後她也說288分鐘真不是人看的,很久。但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事情就應該這麼做,你把它看成是一個行動藝術也可以,或者是折磨別人也折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總之,剛剛說了它是一個探索的年紀,我們也在探索藝術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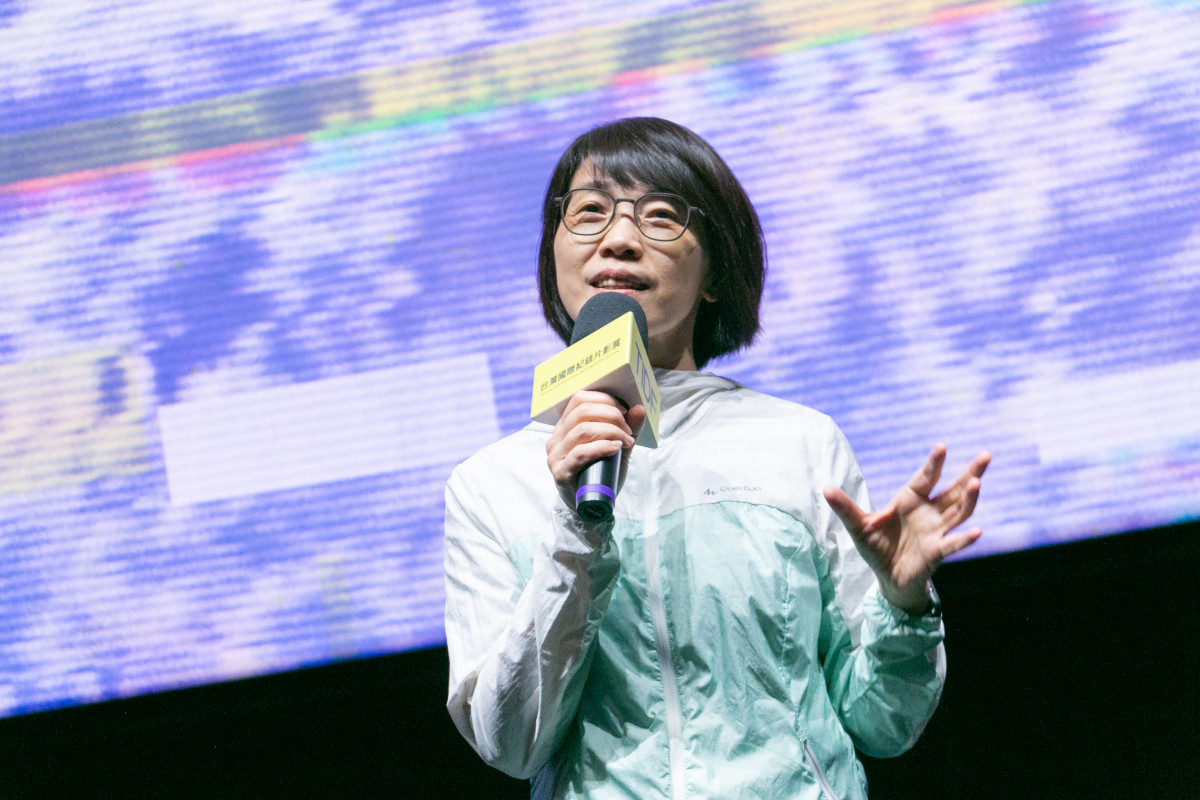
主持人
真的非常感謝兩位真摯的分享,因為時間很寶貴,想先把時間留給觀眾,如果有觀眾想分享自己的看法或是對影片提問,可以提出一些想法。那有沒有觀眾想要提問呢?
Q1
你好,我想針對剛才導演提到關於當時20幾歲很有衝勁去做這個企劃這件事,我現在也是20幾歲,然後有很多人會覺得……現在可能是環境關係,可能是年輕人本質上有什麼改變,好像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那麼有趣的想法和企劃在執行的感覺,這到底是不是事實不確定,不知道導演對這種說法有沒有什麼看法或感受?
周美玲
我們怎麼會批評現在的年輕人呢?如果你想做,就可以開始做。不過志薔他在義守大學當老師,接觸到的年輕人比較多,你的觀察呢?
李志薔
其實應該這樣說,在我們那個世代,所謂的拍攝工具沒有什麼iPhone啊、手機攝影啊、沒有數位相機可以攝影。我們那個年代,第一個拍攝工具非常罕見,就是你必須得花一筆錢,可能現在10萬、15萬,才有辦法買到DV攝影機來做。做底片更困難,底片的機器跟底片沖洗都非常困難,可是那個時代的我們,其實大家更珍惜……的確會非常珍惜這種創作經驗,就是只有一次,然後你要花很多錢,所以會戰戰兢兢地去做這件事情。那如果當然以現在的觀點來看……
周美玲
可是我們那時候一個人只有50萬,要用35mm做一個短片,基本上是血本無歸的。
李志薔
沒錯,所以就是要有熱血。
周美玲
你有賺到錢嗎?
李志薔
沒有,我還自己貼錢。
周美玲
你賠了多少錢?
李志薔
忘記了。
周美玲
所以其實搞創作先要有一個把錢當糞土的心理準備,但是糞土是黃金,所以它也很珍貴。我相信你們也有這樣的熱血啦,我不曉得。所以我們這批導演很多後來為了拍電影都負債累累,我們都是。然後我最多、還負債過3600萬,大概花了10年的時間才把債務還清,很可怕,也沒多可怕啦,人生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不是世代的問題,是你是不是真的有撈到這些不怕死的、志同道合的夥伴,然後正好酒精把我們串在一起,然後我們串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在聊創作,無止盡地聊創作、聊藝術、聊還有什麼可能性、影像還有什麼可能性。而我們都不是念影像的,你(李志薔導演)是台大電機,我是政大哲學,然後我們這些也不是……欸,你(主持人)也不是嘛!
主持人
對,我也不是。
周美玲
你是師大地理。
主持人
對,呵呵。
周美玲
所以沒有侷限吶、沒有框架啊,就是看敢不敢想、然後敢不敢做而已啊!當然人還是要有責任感,還是要預想到如果負債的時候你要怎麼辦,你有沒有能耐可以扛得起來,沒有能耐也是要想辦法扛起來,久了自然就會還清了嘛,要不然怎麼辦。
主持人
對,像是導演說的,我也不是本科生,也還是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做討論,所以真的不要怕,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決心啦,就是某一種我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情,或我想要講一個故事的那種感覺,或許就可以push你自己往前進,也回饋剛剛這位觀眾。那還有沒有其他觀眾有想要再多提問或分享?最後一排角落的觀眾。

Q2
導演好,我其實是算移居今年第七年吧,在馬祖。所以剛才看那個影片我覺得非常有感觸,因為我自己在那邊雖然也沒有多少年,可是因為在那邊做文史工作者,會發現對於馬祖來講,裡面的人都認識啦,就是也變成他們的歷史紀錄。不過我知道這個有12部片,所以也才看了一部分,只是很好奇,不知道兩位導演回過頭看,特別是製作人,這個系列拍下來,到底這12部片,島嶼這個的概念,或者是這12部片最後只在說一個核心故事的話,兩位導演會覺得是什麼?謝謝。
李志薔
我先說一下幾個東西,當初的起源因為這一群創作夥伴的熱血跟浪漫成就了這個計畫,但是如果現場觀眾你們有理解,其實這些導演們那時候是20幾歲、初出茅廬,都還沒有拍第一部電影,但其實現在每一個人、大多數人都是台灣電影界很中堅的人,包括你看周美玲導演、我、陳芯宜導演、沈可尚導演、郭珍弟導演,都有很多部電影,都是在不是非常主流但也都有一定地位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當時的一個創作出口,也是大家磨練創意的一個起步。大家慢慢、慢慢地透過這次的經驗凝聚了一些創作力,每一個人再朝向他最希望的方向去發展。
其實我們剛拍出的那幾年,有去過全世界很多影展,《浮球》是第一個去溫哥華影展的,然後我還有到澳洲啊、到哪裡,甚至在10幾年後,還有英國的影展,因為題材特殊邀到那邊去。我們去參加瑞士真實影展,就非常多、全世界、每一部都去了很多影展,是大家的第一次,也開始慢慢、慢慢在創作上面開始嶄露頭角。我記得以我個人來說,《浮球》算是我第一部導演的作品,那時候日本的新聞還有特派員從日本跑來訪問過我,因為他們對於亞洲的人流、就是人的流動這件事,在中國邊界人的流動他們特別感興趣,做了一個專題,特別飛來台灣訪問我。
你們這個年紀可能不知道,那個時候我也是第一批拍外籍漁工的,還被立委請到立法院去,公聽會就放這部片子。他們那時候在討論如何用人道的方式處理外籍漁工議題,所以其實還是會跟社會有很多互相影響跟交流。剛剛在外面聊說,其實這幾年好比說英國還有某些台灣影展邀我們這些作品去放映,很難想像在24年前的議題,現在還是有持續地發揮它的影響力。
周美玲
然後站在總製作人、總召集的這個身分上,剛剛同學你的問題對我來說非常敏感,立刻令我想起我們那時候交片給公共電視的時候,公共電視的經理質問我的話,他說「你們這12個片子每一支都長得不一樣,然後奇形怪狀的一大堆,它的中心、核心是什麼?」我答不上來,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要大家把核心丟掉,為什麼要有什麼核心?我們就是一個探索之旅,探索什麼是本質啊!探索所有存在的本質、藝術的本質、島嶼的本質、海洋的本質、人類的本質,所有人……所有有情眾生的本質。所以為什麼要有框架?如果有框架,一定是在我這邊我就會提醒、會跟大家說「你要為你的影片找主題,但是我們不用給自己設定框架」,這樣才對啊!要不然我們大家來玩什麼?設定框架就不好玩,就變成是接案子交片,就不是創作了,那就是工作。
那個時候我真的被公共電視交片的那個對象……我們一開始提案的時候經理是袁乃娟,後來經理換成馮姊,馮姊很兇啊,她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可是整個事過境遷之後,馮姊跟我說,她把我罵那麼慘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回頭去跟這些導演們說「你改一下好不好?改一下我們比較好交片過關、比較容易拿到尾款」?因為我心裡的那個概念初衷是很頑固的,我就是覺得這就是我們創作的初衷啊,所以就不斷地跳針重覆我們這些初衷,到最後台內也不得不接受,我覺得很辛苦。當然我現在變成非常理解公共電視那個時候的立場,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才20幾歲,就覺得我只能夠不斷地闡述我的理念,其他的我就不會。
主持人
謝謝。那還有沒有其他的觀眾想要多做回應或是提問。
Q3
導演們好,我想問一下當時各位導演是怎麼決定誰去拍哪一座島的?比如說像李志薔導演為什麼要選擇拍小琉球,其實我也比較好奇,因為雖然是小琉球,但其實是在拍小琉球外海的一座漁船,並不是那座島,所以也比較好奇這個題材是怎麼選擇的,謝謝。
李志薔
剛才有說核心是每一部片子自己去尋找主題,我其實是這樣子思考的,這些離島們大概就是所謂台灣的邊緣的邊緣,所以我其實就在拍一個邊緣的狀態。當初拍小琉球的時候,我一開始其實就已經打定主意不要上島去拍,純粹拍邊緣的邊緣。你不覺得那艘船對小琉球,跟小琉球對台灣是一樣的,或是跟其他離島之於台灣其實是一樣的。我那時候剛當完兵回到台北,我自己在當兵的時候,轄區範圍就有小琉球,我是當軍官,常常會去海巡巡邏,我自己守海防,雖然小琉球很可能2、3個月才去一次,但是我就大概知道那邊有外籍漁工的狀況。那時候就有想透過這個,去拍外籍漁工的狀況。當然一開始設定的時候,也不曉得當中會有多少困難,譬如說語言問題,或是大部分的船組其實不願意讓你拍,然後還有很多運送的問題,但後來我們就一一克服。我自己的思考,其實是從邊緣出發這樣子。
那剛剛講到挑選島嶼題材,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通常我們幾個雖然大家常常在一起、酒友,但年紀還是有點小小的落差,常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有特權就先選。我就跟他說「欸我在小琉球待過,我想要拍小琉球」,就很順利爭到這個。年紀比較小的像陳芯宜導演、沈可尚導演,他們就……沒人敢去拍的就落在他們手上,譬如說陳芯宜導演拿到釣魚台,她就說「慘了,釣魚台我怎麼拍啊?我連上都上不去,我怎麼拍啊?」然後沈可尚北方三島也是,「哇三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我搞不好連上島都上不去」這些任務就落到他們頭上去,大概是這個樣子。
主持人
那我延伸這個觀眾我也想問,美玲導演為什麼會選擇烏坵?是你主動選擇它嗎?還是也是一個被分配的結果呢?
周美玲
因為黃庭輔導演的家鄉是金門,然後偉斯選馬祖也是因為她在馬祖認識那個舞者,所以大家都有一些緣分。沒有緣分基本上就是大家挑剩下的,可是剩下的裡面,當然就有剛剛志薔導演說的,年紀越輕的就是最後會挑剩下的,我應該也是在倒數挑剩下的那幾個裡面。
主持人
好,謝謝。非常謝謝兩位導演特別撥空前來,等下還有一場是「流離島影#2」的放映,如果有興趣的觀眾也歡迎留下來繼續觀賞。
李志薔
歡迎大家來看一看。
周美玲
(現在)有中場休息。
主持人
對,謝謝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