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摧肉身》映後座談
時間:05.12 SUN 10:50
地點: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陳佳琦
出席影人:導演 陳界仁
攝影:王文玨

陳界仁
各位好,很謝謝大家一大早就來看片,然後還有耐心看完,謝謝。
主持人
提醒一下就是我們有翻譯,所以如果有觀眾需要英文提問的話,同樣可以舉手。也許有些人已經知道陳界仁導演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一個當代藝術家。也許也有些朋友並不清楚,可能心裡還在想說我剛剛到底看了什麼。沒有關係,等一下有問題的話都可以盡量的問他。那在開始之前也先簡單的提問一下導演,就是說不管是在這種所謂的錄像藝術或實驗片,或者是到現在這樣子所謂的一個美術館電影的類型......其實我都習慣稱導演為界仁大哥啦,界仁大哥的這個影片呢,其實也會參與一些影展的放映,在電影院裡面播放。但是這一次好像是您第一次入圍到這個國際紀錄片影展喔(註:陳界仁作品《殘響世界》曾入圍2016 TIDF台灣競賽),我不曉得您的心情是怎麼樣?
陳界仁
因為有一部分的資金是公共電視的,所以那個合約上版權就有講他們可以用,所以要謝謝公共電視。
主持人
那參與到這個紀錄片這個領域,不曉得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陳界仁
其實我本來就不會去分劇情片、紀錄片,或者是錄影藝術或實驗片,這些分類對我來講沒有太大的意義。我之所以混在當代藝術圈,只是它比較好混而已,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
好,謝謝導演的幽默。那不曉得有沒有朋友要給一些問題,或者是看完的心得或回饋都可以舉手。
Q1
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我覺得這片好像思考了一些問題,是老師多年來思考的問題。可不可以談一談這個作品在你的思考過程當中,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這部電影一些美術的部分。可不可以談一下,那些像模型一樣的城市是怎麼樣做的,還有背後的想法?謝謝。
主持人
第二個問題是模型,第一個問題是......
Q1
就是這個作品在老師思考過程裡的脈絡。
陳界仁
這個片子它一開頭有一個名字,就是「她與她的兒女們」,這是我一個系列的創作計畫。這個計畫簡單講就是,我們今天其實已經完全進入了AI或網路的時代,人該怎麼繼續下去?前面一開始的字卡裡面,我有提到「公司王國」嘛,事實上,如果我們稍微查一下,或是可能對這方面有研究的人大概會知道,今天全球的實際的狀況是兩家基金公司幾乎就控制了所有的產業。從高科技業,譬如我們以為微軟跟蘋果,是兩家不同的公司,但它背後最大的股東其實是同一個。包括我們以為是美國的、台灣的、中國大陸的不同公司,其實他們背後最大的股東或第二大股東,可能也是同一個。它穿透了所有的、我們以為不同國家的這些界線,但是我覺得我們很少去討論這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我很關心的是我們怎麼認識世界、怎麼感知世界,其實這就決定了我們怎麼去想像未來。但是我們今天從傳統媒體到網路的社交媒體,其實也就是在這兩、三家公司控制底下......這邊就不浪費大家太多時間......所以我們的感知其實就是它們餵養植入我們的。 我想這個是我第一個關心的問題。
那之所以取名叫「她與她的兒女們」,「她」對我來講有好幾個意思。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地之母的那個「她」嘛,每個不同的民族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大地之母,但是意思都差不多。第二個當然就是其實我們就活在這些類似母體或矩陣裡面嘛,我想這個《駭客任務》就談過了。第三個就是我們怎麼去想像一個新的「她」,所以這當然是我整個計畫的想法,我會分序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跟未完吧。因為我預算有限,所以第一章其實2017年就拍完了,但是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人可能對我為什麼要拍這些東西不太理解,當時因為我的預算只夠拍第一部,所以我就想說等2019年的時候,再來拍序章。但後來因為沒錢,還有疫情,所以就拖到現在才拍完。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模型化的問題嘛。我們可以看到美術設計用了大量的模型,從電腦、城市,或者是有實際做的建築物的模型等等。因為我覺得事實上我們的感知、我們怎麼去認識世界是大量的被植入的,我們對事情的判斷也常常是在這個狀況。我覺得這個東西不需要迴避,其實就是某種模式或者模型植入我們了。但是因為它已經變得非常非常日常,所以我們不太會感覺到自己已經是在這個(模式或模型),包括我們的思維方式其實都被模型化。這幾年包括戰爭問題啊,我想其實我們都被模型化。世界應該是非常複雜的嘛,就是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它都應該是非常複雜的,但我們現在其實是越來越二分法,而不是把事情的複雜面展開來。我想大概是這樣,簡單講就是從美術設計到我內在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
我延續岔題問一下,像這次的美術設計,或者是那些模型。你也是一樣是帶著演員,然後大家一起去製作出來的嗎?
陳界仁
這個影片你們看它背景都是全黑的嘛,然後主要是鐵絲網。裡面我們有不同的場景,或者是不同的空間,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戲院這麼大,我們只是把它反覆改來改去做出來的,所以其實一直都在原地拍攝。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我們前期在做這些美術的時候——因為這次因為碰到疫情,所以狀況不太一樣——其實我這麼多年來、二十幾年來,主要大概是不到十個人吧,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一直都是這樣做。你們其實可以發現到——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片子——其實道具、整個場景就只有兩樣東西,一個是鐵絲網,一個是紙箱。第一個是鐵絲網可以移來移去,把它改變成你看世界的,或者是不同的場景。然後紙箱就是很便宜嘛,大概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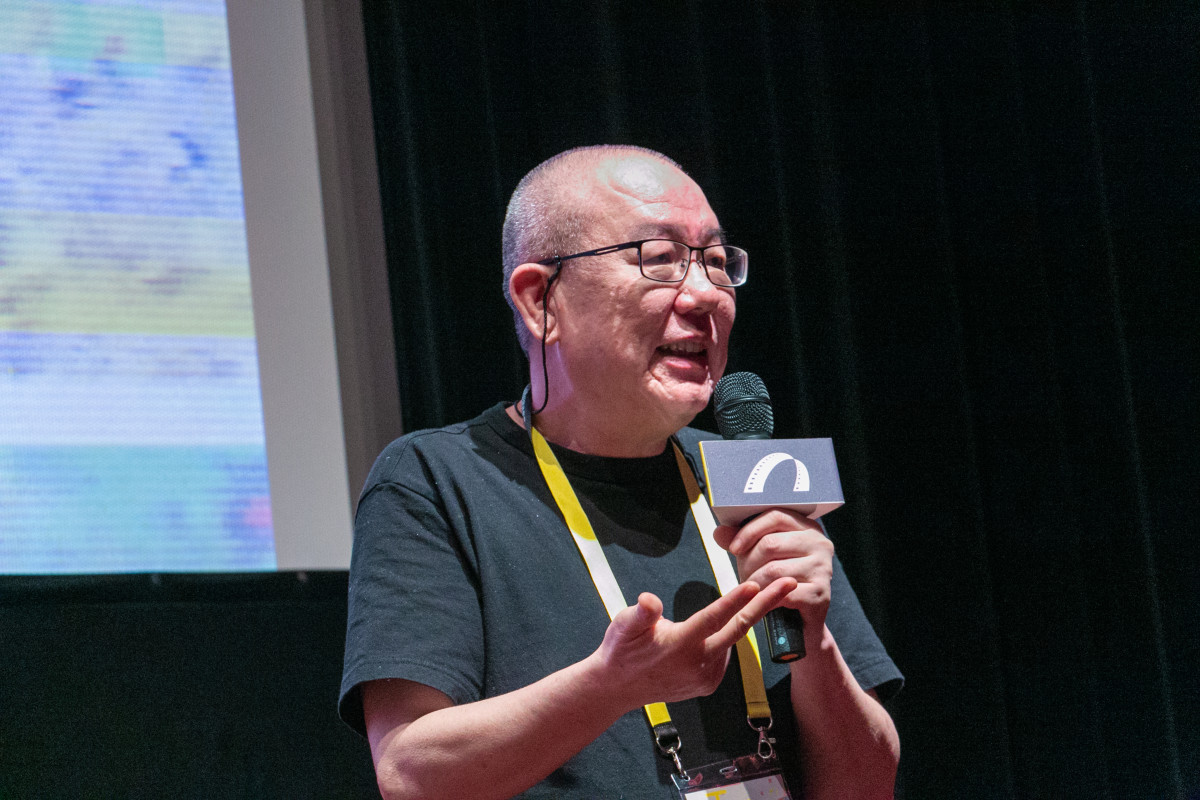
主持人
好,那不曉得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有興趣對導演再提出一些不管是你的困惑,或者是任何的想法?
Q2
當中吟唱的那些語言,有點熟悉又陌生,可以談一下你是怎麼樣去設計他們唱的部分?
陳界仁
最後結尾有一個很長的女生的吟唱,我先講歌詞好了,基本上這位朋友講得非常好,就是既熟悉又陌生。它來自三本經典:一個是《地藏菩薩本願經》,一個是《維摩詰經》,第三個是龍樹菩薩的《中論》。但是這個歌詞,首先它最大的困難是沒辦法翻成英文,我們只能意譯,那就少了中文裡面的那個美,但這也沒辦法。我為什麼結尾會用這個歌詞?當然就是我根據這三本,不是把它硬拼起來,是我再稍微改寫一下。我剛剛講「公司王國」,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被公司王國大量的植入各種事情的訊息:當我們只有三個訊息,我們就只能從三個訊息裡面去做判斷,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老以為網路世界帶來一個去中心化的世界、一個多元的世界,其實只是一個包裝或同質性的,看似多元,但其實是各種包裝的資訊而已,它並不是任何的事實。我們這個影展主題好像是告別真實,是吧?(「再見真實」)其實一切都是人為建構的,形式的多樣性跟真正的多元、真正的複雜,其實是不同意思的,但我們今天其實大量的陷入了形式多樣性......好,我不要用這種方式展開,看看你的問題是什麼?我又忘了。(主持人:經文)對,所以我覺得AI以後的時代,我們再也不可能去做這種什麼真實、虛擬、虛構等等這一類的討論;但從一個比較積極的面向,我覺得它幫助我們,或鼓勵我們、提醒我們,要回到一個人類最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譬如說2600多年前或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期裡面,各個地方不管是佛教、基督教,或者是道教等等,很多那個年代的哲學家們其實都討論過的問題。那我之所以引用佛經作為方法——如果撇開文言文不談的話——就是我們要小心本質主義,我們要反對所有的本質主義,反對所有的二分法,其實這是佛經裡面很核心的用意。那它之所以這樣子講,其實就是要反當時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因為種姓制度就是一種血緣上的本質主義,也就是人被規定了嘛。那當然因為公司王國有各種很複雜的包裝,所以我們以為它沒有本質主義,但事實上,今天的本質主義我覺得依舊是頑強的存在。用一個最直接的就是今天的巴以衝突其實是有本質主義的,而且那種問題從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到今天都沒辦法解決。我想大家可能知道——用巴以或以巴講最清楚——YouTube、Facebook等等是通通否定了,我們其實根本接觸不到這些訊息。好,時間應該到了?
主持人
沒有,還有時間,你很想逃走嗎?(笑)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想要提問也好,或者是回饋也好。在大家思考的時候,也想再回頭問剛剛的問題,其實這二十多年來,你的工作方法好像是有點一貫或一致的,就是大家自己拍電影,然後演員一起做道具、一起排練、一起去完成,這樣的電影工作方法。還有你的這個美學,就是你剛剛講的,好像是看似多變的,我們一直陷在這個形式裡面打轉。可是這二十多年來,你的電影似乎一直維持在一種比較相似的tempo,有一種屬於你的工作方式,但是這個議題仿佛是有一些變化跟差異的。不曉得你怎麼看待你自己這樣的做法?
陳界仁
我是到42歲才有條件拍像這一類的影片嘛,(主持人:《凌遲考》開始,2002年)對對對,所以我在拍片前其實是在想說,我們今天談的這些問題,如果你稍微有閱讀多一點,大家就會知道,其實對我來講,它就是必然會發生的。技術的革命它一定會發生,我們不要以為它不會到來。我很偶然有條件拍片,那時候就想說,我想要做一種「落地掃」,落地掃的意思是以前在野台戲之前,農民他們在農閒的時候,會自己演戲給周圍或者是同村的人看,這種文化生產模式。在那個生產模式底下,每一個人,譬如說這個農民,他既是農民,也是藝術家。他演的角色可能是一個神話人物,或者女性演男性、男性演女性等等,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講他也是一個藝術家。然後第三個是在以前農民起義,或造反的時候,他也常常是一個串聯的媒介,也就是一個載體,他會做一種連結工作,那我覺得拍影片對我來講,其實就很像在做行人落地掃,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深藏我們自己怎麼感知世界的路徑,或者是表達自己的感性,那我們註定就會被類似公司王國這樣的東西,不斷地操控下去。
我再補充一個,我剛剛有說對我來講,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的這些分類不是太重要,因為我覺得重要的是我們提出不同於孔氏王國,或者是所謂主流的意義觀點,就是不同意見的觀點。但是這東西他需要勇氣,大概是這樣。還有什麼......tempo?
主持人
就是你的節奏,或者是甚至我們說的所謂「緩慢電影」這個名詞出來之前,你早就已經在緩慢了,為什麼你會一直維持這樣子的電影形式呢?
陳界仁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緩慢這件事情。我年輕時其實做過動畫、卡通的產業,而且做的還滿不錯的。你作為一個從業人員,你知道這個套路、這個方法是什麼,就是你怎麼吸引觀眾,一直在各種快感中,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然後慢慢、慢慢他就被你帶著走。這其實就是最基本的操控技術,如果大家有讀到一點,就是所謂的「景觀社會」,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操控你、操控觀眾。那因為我做過,所以其實我後來是因為我很厭惡,所以我就不想再做了。當我在拍的時候,第一個就是我已經42歲了,第二個就是其實我我也很少看所謂的文藝片,或作者論電影。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個速度剛好。但是後來我也發現我的速度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再後來是我發現大家以為這個鏡頭好像很長,其實它並不是,它不長,它很多畫面其實根本就只有30秒,甚至十幾秒;大家之所以會覺得很長,是因為它好像沒有事件發生。反而好萊塢有時候(鏡頭)很長,尤其是數位化之後,一個鏡頭可能十幾分鐘,但它中間很多事件嘛,因為它要一直維持一個讓你有快感的方式、可以一直看下去,所以它鏡頭會調來調去。我們對文藝片或作者論講的長鏡頭,不能只從這個字面上去講。但我的興趣,不是這一類所謂慢啊,或者所謂的長鏡頭;我的興趣是覺得每一個鏡頭應該有它,感知這個世界的節奏,或者有它的時間感、內在的時間感。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也就是我們都在此刻,可是我們的時間感可能都不一樣,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樣,那我覺得這個世界它才會豐富起來,或複雜起來。因為我42歲才有機會拍片,然後現在64歲嘛,所以可能對我來講就很自然嘛。
還有一個就是,我希望觀眾可以去注視畫面裡人的狀況,甚至包括我旁邊的道具或環境。因為我們現在都太容易是敘事嘛,敘事就是這故事它過去了,它就過去、過去、過去,其實我們是目不暇接。像更年輕的一代,我想大家用手機看片大概都是1.5倍速起跳,一直在被加速主義這樣帶著走,也就是我只是要訊息,我不要再那麼認真的看一個人。但這個東西或許有一天他到了某個年齡,他就會覺得他想要放下或者好好看。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
好,謝謝導演。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分享?
Q3
陳導你好,可否麻煩講一下這個片的選角方式?
陳界仁
大家可能沒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觀眾:有看過)謝謝。我其實沒有什麼選角,比如影片的主角,因為他就很像我哥哥,所以他從好多年前......其實我拍的影片背後大概都跟我哥哥,或者跟我家人、我朋友有關係,或是我經歷過的事情。那只是因為你越是去經歷過一件事情,你就越沒有辦法直接拍。我可以講一下我哥哥,因為他已經過世了。他其實是從失業得重度憂鬱症,然後到最後是思覺失調,就整個崩潰了。他認為他被監控了,他們會有幻聽或什麼的,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恐怖跟可怕的過程。我上面那個字卡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寫太多字,但就是今天全球大概有1/8還是1/10的人有心理健康的問題。廣義的就是包括腫瘤、憂鬱症,一直到像我哥那種思覺失調比較嚴重。全球現在大概八十億人嘛,那就是差不多十億人有這個狀況,1/8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說全球今天集體的這種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出現了很大的危機。今天這個社會,我們老以為如果有這種朋友或家人的話,就去看精神科,但去看精神科其實沒什麼用,對我來講有一些當然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一些我覺得是因為社會型態改變,我的說法叫做「社會的消失」。中文裡社會的「社」,第一個就是結社嘛,它是有一個關係的,然後我們會匯聚,就是人與人的匯聚、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相互共生,這個環境沒有了,大量的沒有了。我再舉個例子,今天這裡除了有一位外國朋友之外,大部分是台灣的人,大家知道像小學、中學、高中不是都有特教生嗎?現在小學生大概一班都30個,甚至不到30個,平均大概有3個是特教生。也就是說,這個情況它會一直越來越嚴重,我覺得它涉及到非常複雜的問題,可是我們常常第一種是把它疾病化,第二個是如果拍相關影片,到最後大概就是很感人的和解或互相理解,但事實上它是人類的集體問題。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首先要正視的,我講的是根源。
因為時間快到,我再講我的選人,其實沒什麼原因,我就都從我旁邊來(選)。影片的主角是計程車司機,然後裡面有個在爬行的人,他是小劇場裡面很有名的阿忠(鄭志忠)。其實我在24年前,最早談科幻這個問題,是關於未來的,有一個小短片,拍得很粗糙,但其實我本來要發展成一個長片,那個時候他就是其中一個(演員)。這個是序章嘛,第一章其實我們已經拍掉了,他也有演。它們都是像連續劇一樣,我一直覺得我拍的影片都像連續劇,其實每個人物都曾經在前面出現過,他們只是時而出現,時而不出現,但可能在下一部又出現。所以都是從我身邊來的,比如說我會用很多失業勞工,或者是工人朋友,或搞社會運動的,其實就只是因為我認識,然後我覺得某個狀況他們很適合。應該也有人發現,就是這部電影拍得不太像電影,很像劇場,因為我很喜歡這種很劇場化的......第一個是我沒有條件去拍所謂的紀錄片,花一、兩年時間去追蹤,我完全沒有條件。今天你有足夠的時間也是另一種富裕啊,但是我沒有這個條件。第二個就是說,紀錄有時候它有一點痛苦,我不是否定啊,大家不要誤解。它有時候有一個痛苦是你如果要保持倫理的話,你只能拍到他願意展示給你看的,你沒辦法拍到他不願意展示給你看的。比如說我哥這個狀況,如果你要用那種很驚人,或者很聳動、很震撼的,我如果拍那個紀錄片,可能也是拍到他過世為止。他到最後是把房子封起來,把自己活活餓死,然後我們一直叫消防隊、叫警察,破屋而入,但其實沒有用,因為他就是覺得要這樣下去,他就是要走到......讓自己自我解決掉。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是很疲累的。如果用紀錄片拍,當然我也可以用手機等等,看似比較粗糙的方式,但是它會很真實。但是他是我哥哥啊,我怎麼拍得下去?那我就轉一個方式。這樣的一件事情,它帶給我的啟示是讓我去注意、去思考今天這八億人是怎麼產生的——除了天生、生理上的缺憾之外,但在我認識的範圍內,我覺得很多人根本不是——今天社會消失了,他再也沒有存在感,他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其實這就跟日本的下流老人、孤獨死,或者是很多包括自殺率等等,譬如說韓國的自殺率很高,大概就是兩個年齡段嘛,一個是20到30歲的女性,一個是老年人......對不起,我又扯太遠。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問題對我來講都不是自殺,它都是他殺,我就要把這些問題搞清楚。所以就我個人的原因來講,譬如說最後倒在那邊的那個女生,她就是朋友嘛,因為她有參與過一些社會運動,那我覺得找她剛好。不知道耶,我其實就是從我認識的人裡面去想,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
好,謝謝導演。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還有一些不盡興的,也可以在外面再找導演小聊一下。謝謝導演今天帶來這部電影,我想他是把一些比較真實的東西抽離、抽象成一個狀態,意圖使我們去凝視這些人的生存的狀態。裡面也有一些話其實讓我印象非常深刻,譬如說當這些秘密變得那麼公開之後,它彷彿就成為了我們的自然。其實意圖讓我們再去反思,很多我們覺得已經被自然化的東西,還有就是我們是否真的很恐懼被系統拋棄、被共同體拋棄這件事情。謝謝導演的電影,也謝謝今天的大家的觀賞。我們今天QA先到這裡,如果還有問題可以在外面聊,謝謝大家。
陳界仁
非常謝謝大家這麼有耐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