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她們的星球》映後座談
時間:2025.07.13 SUN 14:00
地點:新竹市影像博物館
主持人:翁皓怡
出席講者:蔡華臻
攝影:呂宗憲

主持人
大家好,歡迎來到TIDF新竹巡迴。TIDF去年在雙北舉辦主影展,今年就則帶著主影展的影片,來到不同的城市巡迴,那這一站來到新竹,其實剛好是我們的最後一個巡迴站,接下來到七月底都還會有很多的巡迴影片放映,大家可以把握最後可以看這些片的機會。那大家剛剛看到的這部片《沒有她們的星球》其實是去年的競賽片,然後去年導演也有來到台灣跟觀眾交流。那這部片也獲得去年的TIDF「青少年評審團獎」和觀眾票選獎。那不知道大家剛剛看完有什麼感受?雖然這次巡迴沒有辦法邀請到導演來到現場,但是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角度、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分享,讓大家從不同的切角觀看這些紀錄片,所以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的是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蔡華臻老師。老師研究的領域包括性/別理論、女性主義,以及全球化移民等。這些母題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在片中看到,比如導演有提到說,在伊朗推翻君主制度之後,女性反而要戴上頭巾,開始有非常多的人口需要遷移或是面臨流亡、離散;然後包括她身為一個女性導演,如何在這之中自處;以及可能不只是人的移動,包括大家可能最有印象的是導演去購買其他人的「二手」電影膠卷,這件事情就顯示了當電影作為一個實體媒介本身,這個實體可以被這樣子流動、移動,而其中承載的記憶文化,或甚至歷史也就這樣子被傳承下來。我覺得這件事其實也是非常有趣的,那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歡迎華臻老師!
蔡華臻
各位好,我是蔡華臻,那今天非常高興在TIDF來新竹的這個非常特殊的場合跟大家分享我對這個電影的看法。那我相信各位剛剛看了也很有感覺,那這個電影對我來說,最有趣的就是說,它不僅是個紀錄片,事實上也是所謂的「論文電影」essay film。那「論文電影」基本上它是晚近研究紀錄片的學者提出來的一個比較新的概念,那一開始他是Timothy Corrigan,他是賓州大學的一個退休的教授(提出的)。那什麼叫論文電影?就是我們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你會發現說這個電影其實非常個人,尤其一開始對不對?那一開始我們就看到這個電影導演,他把他的出生跟伊朗的歷史連結在一起,他說他事實上就是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那年出生。那從這邊開始,然後我們就會看到事實上有好幾個不同的、很有趣的歷史的交織:一個是他個人跟他的家庭的歷史,對不對?我們看到他的媽媽,事實上有阿茲海默症,那所以這個時候,這個電影它一直在討論的,關於如何地記憶歷史跟抵抗遺忘的問題,又多了一個向度;那另外一個層次的歷史是我們在電影裡面不斷的看到的,是伊朗女性的抗爭史,比如說我們看到1979年之後的他出生的片段,之後事實上我們馬上看到的是照片,然後裡面還有好幾次,比如說有一段是2008年,那個時候事實上伊朗有所謂的一個「Green Movement」,那我們在台灣比較少人知道,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抗爭,然後到2022年又有一次非常重要的uprising(起義),那一次事實上是因為有一位女性沒有帶頭巾,竟就被警察殺死了,所以另外一個貫穿的歷史,事實上是這些不斷地持續,但是到目前為止還在進行的革命;那另外一個層次的歷史是什麼?事實上是就我看來,很有趣的是,它同時也是關於影像媒體的歷史。一開始我們看到黑白影像,我們看到一群在伊斯蘭格命之後抗爭的女性,從那一個moment開始,事實上,這個電影也開始把這個導演她自己跟她個人的命運跟歷史跟伊朗女性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那之後我們還看到什麼?我們看到包括他去蒐集一些超8mm的影像,以及很多後來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的各種「小規格電影」——我們今天會這樣說。那還有什麼?還有事實上是數位時代的影像。那各位還記她如何的描述她如何成為一個filmmaker嗎?她事實上是把她去讀電影學校這件事情放在這一整個系譜裡,這一整個影像媒體史跟抗爭史跟個人史交織的一個脈絡裡面。所以他的第一個攝影機是上什麼各位還記得嗎?是一個HTC的手機對不對?那所以我們事實上從類比時代的影像,一直看到數位時代影像,同時一直在思考的是什麼我們如何在當代的——不只是電影研究,還有文化研究——一直在思考是,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歷史跟所謂的「archive」(檔案影像)的關係?那這個「archive」講的事實上是所謂的非官方檔案,不是去檔案局看的檔案,而是私人影像對不對?是無論是製作跟流通,都是受到壓制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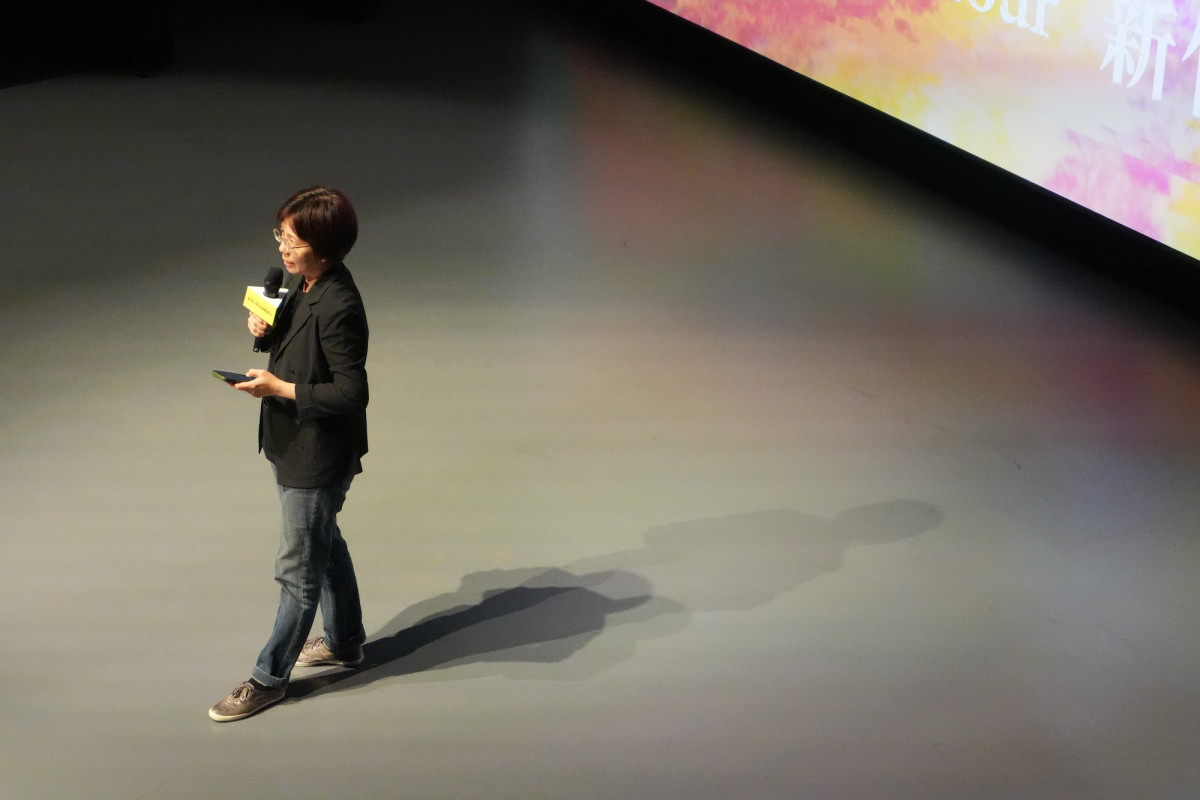
所以在這個影片我們會看到,事實上它很多畫面,尤其到最後,我們看到很多有一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們看了都很有感覺,就是很多人開始分享他們的家人,以及朋友死掉之後那個跳舞的畫面,那這些畫面事實上同時跟這個導演他如何描述她怎麼樣開始拍電影(有關)。各位還記得嗎?他剛拿到一個HTC手機的時候,非常開心地開始從他自己家開始拍,那你看到的是什麼?是看到他跟他的家人在抓蟑螂,事實上是很小的在家庭內的事件,因為通常不會被放到所謂的官方大歷史裡面。然後再來是什麼?跳舞這些在官方歷史裡面被認為不重要的事件,社交的影像,那事實上,在這個電影的後面,我們也慢慢的看到說,不論是這個導演,她自己拍電影這件事,包括事實上尤其在Covid-19那一段,人們如何地傳播跟分享影像,它變成一種新型態的建立人跟人連結跟建立社會性的方式,那我個人覺得那個部分事實上是非常有趣的。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其他的記憶歷史的方式,比如說導演的媽媽,雖然導演有在她媽媽得了阿茲海默症之後教他如何用手機對不對?但是這個媽媽她有她自己的記憶歷史的方式,那是什麼?就是織圍巾。所以我們同時看到其他的記憶歷史的方式,比如說織圍巾。事實上,唱歌也是,甚至跳舞。那導演她除了自己是個導演,她事實上也是個非常專業的剪輯師,對不對?所以透過她非常巧妙的剪輯,我們會看到這些非正式的,不論是勞動,或者是被歸類為娛樂的行為,都變成一個層層疊疊的記憶,由日常的身體性的行為跟活動來記憶歷史的方式。
那裡面有一段很有趣,因為在講到那個有一個在美國的學者,就是Lela那一段對不對?那跟她這個學者呢,因為流亡到美國之後跟這個導演聯絡,那在這個時候呢,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交織點,因為在那個在那個moment,關於這個導演,他不斷地在collect(收集)的那些東西,好像突然突然有了一個活的連結,對不對?那我們看電影,看到最後發現,這個導演事實上她也回不去了。那我不知道各位你還記得,她要離開的那一天有一些鏡頭,事實上是拍她家,那我在看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說那個是她拍的,還是說是事後她請她的朋友拍的?因為事實上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它也隨著影片的進行,會發現說,這一個關於使用影像來記憶的行為,已經不只是這個導演個人的行為,它變成一種集體性的行為。包括說她的媽媽過世,那事實上,這個導演她已經流亡了,那以及說等她待在德國基本上回不了伊朗之後,那在伊朗的一些抗爭的畫面,也不是她拍的,所以這個時候,她這個個人性的拍攝電影的行為已經成為一個集體性的行為,變成一個集體性的書寫歷史的行動,那這也是我個人覺得特別地重要的地方。

那我自己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有關於最後的畫面,我自己其實有一點疑問啦。對那不知道各位怎麼看?因為在這個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一個小女孩,對不對?那拿下了頭巾,以這個陳述的方式,她其實可以是任何人,對不對?可是她也可以是這個導演。那基本上對我來說,它就是這個電影的中心,它如何地把從個人出發,我們說論文電影,它是一個非常強調拍攝者的個人主體性,以及個人的觀點的一種電影,但是它同時也會常常在思考影像本身是什麼?影像跟這個拍攝自身的關係是什麼?以及以這個電影作為case的話,影像跟歷史的關係到底是什麼?那我們在這個電影裡面不斷地看到這種個人的跟集體之間記憶跟歷史的交織,以及到最後filmmaking(電影製作與拍攝)本身事實上都是一個集體的,不僅是建立連結的方式,也是集體的拒絕遺忘的行為。
那我個人在看那個導演的媽媽過世那段,我非常、非常有感覺,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說在那一段,事實上它是沒有現場音的,那你只看到說,這個電影越到後來,你其實可以越感到這個導演的孤單,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而且到後來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她自己的自拍,以及在那個,他透過手機跟她已經回不去的伊朗的家人跟朋友對話。包括說她媽媽到後來事實上已經快要過世的時候,我們看到說她媽媽開始其實有一幕是她媽媽已經躺著,對不對?那這個時候這個已經快要失去行動能力及意識的導演的媽媽,事實上她做了一件事,我覺得那件事非常的,就影像理論來說非常有意思,但是也非常感人,就是你想這兩個人——導演跟她的媽媽——分隔兩地,那透過這個手機,他們如何傳達對彼此的思念?那事實上是透過親吻,對不對?那這時候這個導演媽媽她已經躺著,你想她是一個即將要失去意識的人,她做了一件事是什麼?她去碰了那個螢幕。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那為什麼這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因為在我們當代的電影理論一直在講說,觀影經驗它不僅是個視覺經驗,它也是一個事實上也是具有觸覺性的感官性的經驗,那我覺得在那個moment非常有趣地展現了這個東西,就是透過透過一個小小的手機的影像,這我們看的是大銀幕,那我們看到這一個不可能的碰觸,事實上是經過手機、經過影像的中介來完成。那事實上在那之後,再接下來我們應該看到的就是她媽媽已經過世了。那我個人覺得這個地方非常動人,那事實上它這一個畫面也是對我來說,在這個電影裡面,最關鍵的一個,關於影像的思考,就是如何地透過就算是小規格電影,或者只是手機,如果如何透過這些小小個人的日常的影像,碰觸到他人,完成歷史書寫的工作。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主持人
謝謝老師,好,那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有想要回應的?也可以分享你們的感受,或者是對華臻老師怎麼看這部片的其他疑問,都可以舉手,然後我們會把麥克風遞給你。
好,大家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思考跟消化一下。那就是我也回應一下老師剛剛提到的內容,因為剛好去年我們有做這個導演的訪談,然後其實導演也自己也有特別講到,就是關於最後一個鏡頭,就是他放的最後那個小女孩的畫面這樣,以及他去年得了我們的「青少年評審團獎」,等於是一群台灣的青年選出來最喜歡的片這樣,當時導演其實對這個獎項是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她覺得她其實在剪接到後面的時候,已經有點覺得不太知道該怎麼辦,然後其實她那時候也回不去家鄉,所以其實她也很感慨,不太知道如何剪下去或是拍下去,真的有什麼意義嗎?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或是自己如何去抵抗遺忘這件事。但後來她放了最後一畫面是這個小女孩的鏡頭,其實她一直想要說的是,當她在街上看到一樣有這麼多的年輕的女孩們和青年在革命和在努力的時候,是讓她覺得最有希望和力量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個青少年評審團獎對她來說是一個這麼大的鼓勵跟殊榮。好,那我補充到這裡,那大家有沒有其他想要回應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問題?不管是關於這部片,還是關於其中導演可能提到的歷史。
Q1
非常感謝這位主持人和老師。然後我的問題就是,我看到好像就是在影片中,她媽媽在過生日的那個片段,好像他們是帶著頭巾的,然後我就覺得很好奇,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影片還有一個內外的區別,就是內是她自己的世界,然後是一個比較自由,然後不需要戴頭巾;然後(外)就是一個宗教的,然後威權的一個世界。那為什麼就是在那個世界裡面的媽媽就仍然還是會帶頭巾過這個生日?這是我比較好奇的第一個問題。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就是我非常為這些就是勇於去抗爭,去上街,然後去抵抗這種父權制的這些女性,就非常佩服她們,但是另一方面,我會去想就是因為一些,就是去反思西方女權主義的一些,所謂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他們會去想,就是好像在西方女權主義裡面,他們只會更加關注,或者更加看到,這些就更符合西方式的這種抗爭政治的這種女性,那麼那些就是如果是那些沒有上街的女性,或者是在這種政權體制下,他們態度更為曖昧的女性,他們如何被看到。

蔡華臻
OK好,謝謝你的問題。其實我個人在看的時候,我也有想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如果以後殖民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來說,這個電影如果沒有處理好,它滿容易落入一種,以一種刻板印象的方式,去討論伊朗女性的壓迫。那我覺得這個導演她事實上有思考這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尤其從他選擇的那一些,比如說他買到的一些所謂的unofficial archive(非官方檔案影像)、一些超八的電影,她選擇放哪一些片段,以及她自己選擇她拍的日常生活放的是哪些片段。然後她放的事實上都是比如說跳舞,對不對?那這個跳舞包括說在私人領域。但是也有比如說有一段那個super 8(超8影像),事實上有一個女生穿的非常性感,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那個應該是在公眾的場域,對不對?好那以及說,比如說她放的一些,比如說他過生日的,然後他的朋友寄影像給他,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電影裡面看到的伊朗女性其實是非常頑皮的形形色色,然後非常地有活力,所以並不是,我個人在看的時候覺得這個電影它並不會落入那個把伊朗女性放在一個需要西方女性主義者去拯救的,那一種典型的受壓迫的位置,我們看到的是非常具有能動性的女性。那同時這個電影它也不是只有關於伊朗女性被壓迫,因為我們其實也有看到一些交叉的,比如說在影片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事實上一個男性被處決,那在後來我們在錄像時代,我們也看到也有一個男性在街上就被打死。所以我個人覺得它,這個電影倒不會這麼輕易的,就是講的那個就是「我們要拯救被壓迫的伊朗女性」的那種第一世界女性的刻板印象。
主持人
那個二樓的觀眾。
Q2
不好意思,大家好,老師你好。然後想要問一個問題是,因為在那個電影裡面一直有出現美國相關的一些,就是可能是「打倒美國」或相關的這種看板這樣子,然後他自己在自己的回憶裡面有講說她上小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他怎麼去喊那個口號,就是「我們要恨美國」類似這種口號這樣子。然後雖然我覺得這不完全是個電影的整個基調之一,但我也是滿好奇,對於自己的國族的意識認同跟她身為女性,她可能是很愛自己國家的,但是她的國家,或是她的政府,卻對女性做出這麼多不合理,然後非常殘害人權的事情,然後她在這個縫隙裡面,我也沒有感覺到她完全就是說我們就是要擁抱西方那一套,但是她找到了一個縫隙,然後去表達自己的那個夾縫的那種感覺,然後這個部份也是我自己看完了以後,也覺得他處理的非常好的其中一個點這樣,那不知道老師有什麼看法?謝謝。
蔡華臻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那在影片裡,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搖滾樂其實蠻重要的,對不對?他們有一段在唱的是那個Beatles的,所以基本上從這個影片呈現出來的東西,一方面美國在作為官方敘事裡面的邪惡的代表需要被打倒,但是一方面所謂的,因為知道我們在思考什麼叫做全球化的文化的時候,常常會有一種輕易的二元對立,對不對?那這個電影就像這位朋友剛剛說的,事實上,它非常的,我會說它非常巧妙的,在處理的是說,因為它也沒有去歌頌所謂的美國或是西方的文化,對不對?雖然我們有看到搖滾樂的精神,它的叛逆精神是留存的,而且是以在一個私人領域的方式,人們聚在一起,唱卡拉OK的娛樂的方式作為中介,但是它也沒有去全然地擁抱所謂的跟伊朗二對立的所謂的美國或西方的價值。所以它的確是非常巧妙地在處理這些女人如何地在這些不同的,關於比如說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所謂的西方文化的論述,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它如何去處理這些不同的東西。
主持人
還有觀眾有提問,或者是想法想要分享的嗎?沒有,好,那也剛好時間的關係,我們看華臻老師最後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再補充的嗎?(蔡華臻:沒有耶)
好,那就是剛剛也非常感謝華臻老師很精彩的分享,其實聽到後來我也一直覺得老師提出的那個從個人、私人影像,或個人在講自己主觀意識的論文電影的調性,發展到最後,反而你其實是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確定說拍攝的人到底是誰,然後每個人好像都可以拿起攝影機開始記錄,而這將會成為所有伊朗女性或所有伊朗仍然在抗爭的人的集體歷史。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可能不只這部紀錄片,包括現在很多可能不論是巴勒斯坦,還是世上各個面臨威權壓迫的地方,所拍攝的相關紀錄片或影像,我覺得都可以看到很多所謂「持攝影機的人」的模糊,然後所有人好像都跑到這個攝影機後面,也就好像都把自己的歷史寫下來,非常令人感動。
最後就是新竹巡迴是今年TIDF巡迴的最後一站,所以就是真的是最後大家可以補去年沒有看到的電影的機會(笑)。接下來到七月底都還有很多場放映,那如果大家是對,比如老師剛剛提到的這個essay film這種論文電影/散文電影有興趣的話,後面下個週末還有整個「流離島影」系列的放映,它也其實代表了2000年代我們台灣自己開始出現一些更有個人主觀性,然後比較接近西方概念所謂的「論文電影」的敘事方式的片子。所以也非常非常歡迎大家繼續來影博館看片,好,謝謝大家,也謝謝再次熱烈掌聲謝謝華臻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