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歧連線:《旱地焰火》&《臨時工》導演線上座談
時間:01.29 (SUN) 20:00-21:00
主持人:林木材(TIDF策展人)
導演:《旱地焰火》喬安娜.皮門塔、阿迪烈.奎羅斯、《臨時工》許慧如
與談人:葡萄牙獨立策展人Cíntia GIL、UnionDocs
林木材: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TIDF與紀錄片社群UnionDocs合作的【藝歧連線】(Artistic Differences)活動,在一月初我們放映了《旱地焰火》(Dry Ground Burning)這部巴西作品,兩位導演Joana跟Adirley也在線上,在台灣部分我們選了許慧如導演的短片《臨時工》作為放映搭配。
一開始我想先請線上夥伴們跟大家打招呼。因為是全球社群,所以有時差。現在是台灣的晚上八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木材。請大家簡單介紹,講一下自己在哪裡、幾點鐘。先請兩位發起人,UnionDocs的夥伴Christopher跟Jenny跟大家打招呼。

Christopher:嗨大家好,很開心能參與【藝歧連線】活動,跟大家一起對話,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和Jenny Miller同時上線,她是我在UnionDocs的夥伴,還有Cíntia Gil,她是我們這次合作的策展人。
Jenny:大家好,很高興能參加。我們這邊在紐約市是早上七點。接下來交給Cíntia。
Cíntia:大家好,我在里斯本,這邊是中午十二點。感謝你們來看片,也感謝TIDF的邀請,木材與Zoey等團隊成員的安排。
林木材:謝謝。我們現在請《旱地焰火》兩位導演Joana跟Adirley跟大家打招呼。
Joana:大家好,我在波士頓,這邊是早上七點,跟Christopher一樣時區。很高興參與線上論壇,也謝謝各位的邀請與協助。
Adirley:很高興來這邊,謝謝大家。
林木材:最後還有一位來賓,短片《臨時工》導演許慧如,請阿如跟大家打招呼。
許慧如:大家好,我是《臨時工》的許慧如,我在台灣,目前是晚上八點,是比較好的時間,不用像大家很早起床。也祝大家新年快樂,因為我們剛過完農曆新年,今天是初五,是在我們習俗裡要開工的日子。剛好有這個會議,透過影片來對話,開啟今年的工作,我覺得很棒。
林木材:那我們言歸正傳。這是一個UnionDocs跟Cíntia共同發起的活動,TIDF只是夥伴之一,我們放映的這場是【藝歧連線】的亞洲第一場。先請Christopher、Jenny或Cíntia,跟我們介紹活動的原始構想、希望達到的目標。
Christopher:UnionDocs是一個紀錄片中心,我們大本營在紐約,辦理許多活動、工作坊。決定舉辦【藝歧連線】,是為了促成一個真正的、更好的國際對話,讓看電影更有挑戰性,更激發深度討論。我們的對話不是一次QA而已,是從觀看影片開始,然後舉辦線上讀書會,也有舉辦實體放映,再與我們的影展夥伴合作,邀請導演來對談,最後將成果做成一個podcast節目。這是我們的形式,是一個從節目延伸出來的活動。
Cíntia:【藝歧連線】想讓影片盡量在各地傳播,連結不同的人跟想法,藉此去思考一個國際社群的可能樣貌。最重要的是,讓大家成為朋友,讓友誼發生。這項活動去年八月就開始了,在科索沃與Dukufest合作,當時放映了一部葡萄牙片跟一部科索沃片。然後去英國的Open City紀錄片影展,放映了兩部美國片。再來是去智利,放映一檔墨西哥電影節目,來自一個60、70年代的女性主義電影團體。接著就是台灣的TIDF,TIDF是一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影展,我們很敬佩你們的成績,也覺得如果能把一部台灣電影跟我們選的電影一起放映,能創造很有趣的對話,於是就有了巴西電影《旱地焰火》與台灣電影《臨時工》的聯合放映。接下來,我們要去柏林影展的影評人週,目前已經宣布會是一批70年代的巴西短片,由Aloysio Raulino、Paulo Rufino、Ana Carolina等拍攝,他們對外界比較陌生,但都是很傑出的電影工作者。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大家參與。
林木材:台灣觀眾不是很容易看到巴西作品,就地理位置來說也很遙遠,搭飛機要二十小時以上。透過電影去了解這樣一個不同地方的文化與社會,也許是一個更有效的方式。剛剛Cíntia有提到文化交流很重要,想請你再聊聊,為什麼特別選《旱地焰火》給大家看?
Cíntia:坦白說,比較是直覺。七年前我去TIDF的亞洲視野單元當評審,那時的片單讓我感受到形式的自由,留下深刻印象,也學到很多,讓我去思考電影跟現實的關係、電影中的記憶是什麼等。TIDF選片的多元、想像力、自由,讓我大開眼界。我覺得《旱地焰火》能回應這種選片的自由。還有地域也很重要,TIDF似乎特別關注地域、人與居住地方的關係,《旱地焰火》也是這樣的片。而且,我也覺得你們的觀眾對於不同電影形式的接受度很高。
林木材:我們策展團隊看了《旱地焰火》後,非常驚訝。形式融合虛構跟真實,就導演說法來講,也有一點田野調查跟民族誌影像方法的使用。當我們試著挑一部片去回應,就想到許慧如導演的《臨時工》,也是有一點在虛構裡面去呈現了真實樣貌。在空間展現上,也是發生在都市邊緣,比較沒有辦法被管理跟治理的都市角落。兩部片一起放映,相信觀眾對於地理空間、人的認同與身份,會有很多想像。是不是先請《旱地焰火》的兩位導演,來談談創作方法?這方法是一開始就想好了,還是在某一個階段,才突然想出這個形式更適合你們想講的故事?Joana現在不在線上,可能去照顧小孩了,那我們先請許慧如導演分享。
許慧如:剛剛聽到Joana導演有一個baby要照顧,就想到拍《臨時工》的情況。那時我也是一個要照顧兩個小孩的媽媽,所以有一個很現實上的困難,沒辦法如過往拍紀錄片以長期蹲點製作。當時就有一個念頭,想透過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拍紀錄片。還有就是,長久以來的紀錄片製作過程,總是有一個道德問題非常困擾我:當你要去拍攝「別人的」生命故事,來成為「你的」影片素材,這件事對我一直有一個根本上無法解決的道德困難。那時就希望有一個方法來解套,才有這個形式發想。就是我們應徵這些臨時工,他們來被拍等於是做一件工作,每天付他們工資,完成工作後,他們又回到自己的生命脈絡裡面去。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形式來完成一部紀錄片?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影像上的冒險。
林木材:這部片也是用「臨時工」,這個不管是身份上、社會上的存在方式,作為一個形式來回應。接著請Joana跟Adirley聊聊你們的創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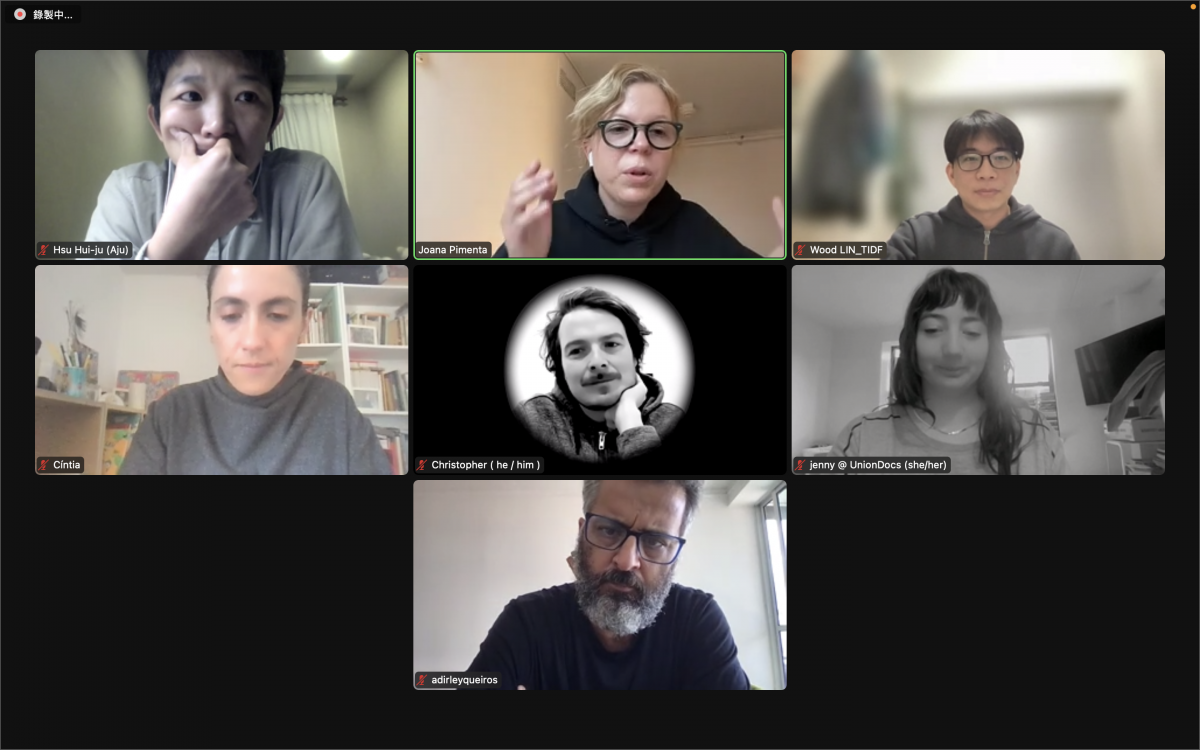
Joana:這部片採取的形式、跟素人演員合作、介於虛構和現實之間的想法,在一開始就決定好。Adirley或我之前拍的片,都對真實的可能性很感興趣。我們沒有要去區分虛構與非虛構,這兩者可能在電影誕生時就處在模糊界線,我們更想在一個開放的過程,不知電影將會帶我們走向何方、我們將會遇見誰並且將之納為電影的一部分之下,去找出兩者可以提供彼此什麼可能性。這部電影跟之前我們拍的電影相比,一大差異是更不確定要怎麼拍,視演員能提供我們什麼、電影能做什麼、不是歷史曾是什麼(was)反而是歷史可以是什麼(could have been)而定。演員提供給我們的故事,他們說是真的,我們就相信是真的,盡量組織進來。我們沒有照劇本拍,但每天會把要拍的情境告訴他們,會重拍幾次,有時重拍一整個場景,有時在不同地方重拍,有時甚至重寫一些對白再拍。跟我們合作的演員,以及他們想帶進來的故事,有些是有政治性的。例如很多人進過監獄,我跟他們保證,攝影機會持續拍他們,他們會持續出現在片中,這部片不會捨棄他們。所以,這部片不是關於他們的脆弱,片中他們就竊取石油,與國家為敵。這對於素人演員來說有更多自由,他們帶入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詮釋。不是要展現你的脆弱,沒什麼好可恥,坐過牢並不可恥,反而能創造出一個政黨,我們試著把這些都放進敘事內。之前拍片會擔心放入虛構有影響,但這次完全不考慮,從一開始就把界線模糊掉,玩得很開心很自由。雖然每一刻都不確定,但我們利用這個不確定。Adirley,你有什麼想補充?
Adirley:不同形式的混合,是想要把瑟蘭迪亞這座城市的歷史放進來。這城市有一些歷史與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不過在電影中有可能實現。這部電影不滿足於只以虛構電影或紀錄片這樣的傳統形式來拍,因為那些敘事慣例或既定的生產模式,都是由長久以來的掌權者建立出來的,而這些敘事方式也創造了過往被述說的城市歷史。傳統的敘事慣例或既定的生產模式,其實有一種非理性層面,會將這座城市的特定歷史與故事面向折疊起來,因此我們想要遠離這樣的傳統。
林木材:謝謝兩位。這個活動在之前也先舉辦了讀書會,成員來自全球各地。UnionDocs擷取了讀書會中的觀察,做成兩分鐘的影片片段。
(播放影片〈Means of Ordinary Disruption〉)

讀書會成員1:我們談到兩部片的連結。我們談到摩托車,摩托車控制了公共空間,對於居住在邊緣地區的人,摩托車是交通工具,也可以說是一種掌握自由的象徵。
讀書會成員2:在我居住的地方,摩托車非常重要,背後有龐大的運作與組織在支持。摩托車不只載人,也是整個社群的重要部分。
讀書會成員3:我們也談到「義肢」的物件概念,摩托車就是一個例子。摩托車有輔助功能,替代了人們受創或流離的部分。義肢這個物件,或許能象徵失去權力的政治場域,因為摩托車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失去,或是填補空缺。
讀書會成員4:Tanya剛剛提到「解除不再需要的東西」,我馬上想到影片描述的現況,人民被移到社會的邊緣地區,被消除或解除,我也會從這層面來解讀。
讀書會成員2:我舉一個例子,我住在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市的原住民社區,可以説是一個邊緣地區,但我也住在社區的中心,「邊緣地區的中心」,聽來有點矛盾,但就像這兩部片的角色,他們既處於邊緣,也是主角、觀眾認同的對象。
林木材:剛剛看到的是讀書會的觀察。Cíntia事實上也算是讀書會的主持人,她把讀書會定位為「擾動日常的幾種方法」,大家針對這個題目去觀察這些片。她也引用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編撰的一本書,好像沒有中文出版,英文叫《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去說就算是批判,也不能只是旁觀者,要介入事件去做擾動。我自己是這樣理解,兩組導演用的方法,不只是很單純的虛構,這個虛構會去回應現實,甚至讓主角游移到本來的身份跟空間裡,所以這裡的真實變成有非常多層次,我覺得是片子很成功也很有趣的地方,顛覆了電影慣有的敘事型態,也讓我們看見一般在所謂的邊陲跟邊緣看不見的故事。慧如導演,你剛剛聽他們講的,還有讀書會成員的觀察,有什麼想回應?
許慧如:我覺得這兩部片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臨時工》我不覺得有虛構成分在裡面,比較是創建一個舞台,濃縮某一些臨時工的背景、場景、生命故事在裡面,透過我們去安置一些事件的發生,他們也自然地像是跟我們共同即興創作了這個舞台,以及其中發生的所有事件。我會覺得比較有趣的部分,的確是那個有機的共同生長過程。現在回想,還是覺得不可思議。剛剛Adirley導演提到,如果過去的紀錄片拍攝比較像是某種權力的宰制關係,那我會覺得在《臨時工》內的顛覆,是一種更開放的轉向,更不是由我們掌握攝影機的人去主導一切事件,而是共同去發生跟完成。
讀書會提到摩托車是我的意料之外,但我覺得非常有趣。摩托車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很習以為常。但是當一個其他國家觀眾的角度看到這件事,很有意思的是,這又回應到關於邊陲處境,因為高雄一直被當作工業城市,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又老又窮的城市。其實這片子開始會拍攝,是因為這些工廠在當初使用過後,如今都已廢棄。在台灣,高雄是有最多廢棄廠房的地方,包括那些尋找臨時工的塗鴉、廠房、臨時工本身,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裡,都處在一種用完即丟的角色裡,只是一個「臨時」的勞動力,使用後就被遺棄。所以,這幾年當高雄在轉型時,我們會看到這些景象在快速消失中,包括我們拍攝到的工廠,很多都在這幾年被拆除。談到摩托車,人們一直被驅趕,這些在城市中屬於骯髒、醜陋、老舊、貧窮的東西,一直被趕到邊緣。比如高雄有捷運,但捷運會到的地方是百貨公司、藝文中心,是臨時工們不會去的地方,所以捷運使用率非常低,大家還是習慣用摩托車去抵達很多地方。摩托車可能某種程度象徵自由,但也反映了階級處境。對於臨時工來說,我覺得摩托車更像是肢體的延伸,或是最小單位的家,它可以載你到任何地方,可以讓你躺在上面看手機,進行最小程度休息,讓你載著你的工具、完成的東西離開。被注意到這點,我覺得很有趣。
林木材:謝謝。剛剛講虛構可能沒有那麼準確,應該講這兩部片都有對真實與現實的情況進行一些調度,經由這些調度之後,產生更深層的東西,去挖掘現實。也請《旱地焰火》兩位導演,針對讀書會有沒有要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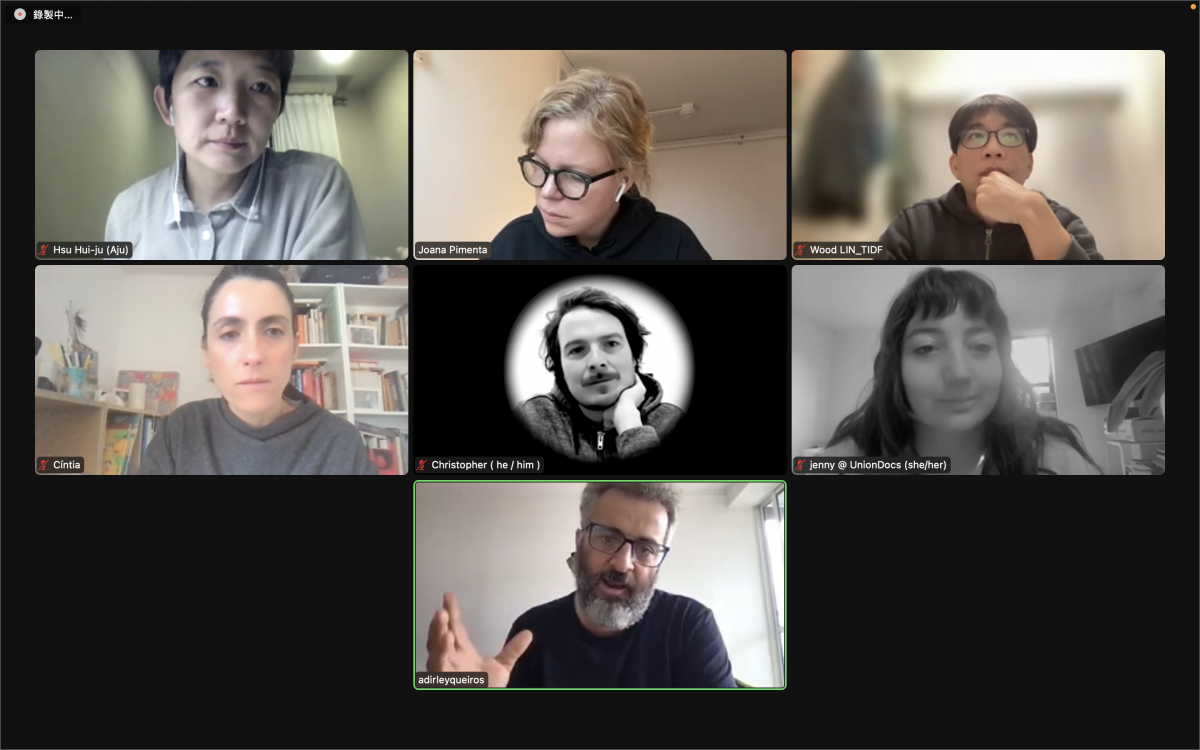
Adirley:《旱地焰火》的摩托車騎士,很接近Lumpenproletariat(流氓無產階級)這個概念。摩托車在我們電影的脈絡下,跟他們的勞動活動緊密相關。這跟《臨時工》有點不同,巴西的臨時工狀態也不一樣,在巴西除了聖保羅之外,不太存在工業城市,巴西利亞是政治首都,其他是以商品經濟與運輸為主的城市。片中的摩托車騎士樣貌、居住場所、機械場景等一切,是我們想來打造看看讓一種熱門工業發生在此會怎麼樣,竊取石油也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談到這些機械交通工具,在古巴他們會把不同汽車的零件重組成一台汽車,這些摩托車也類似,因為他們很窮,通常沒錢買輪胎,就從別台車拆來用,所以這些車成為很怪異與獨特的視覺物件。摩托車在巴西與邊緣地區的群眾有關,也跟自由有關,但主要連結的是勞動,不是休閒,是擁有自己的勞動工具。摩托車在巴西帶有政治性,摩托車族群幾乎成了另一個國度、另一個階級。不過這樣的自由,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種反常思考的錯覺:騎士擁有自己的摩托車,好像就能成為自己的老闆,能按照自己的時程工作,但事實上,你也是進入了新自由主義下的工人邏輯。
林木材:摩托車是我每天上班的工具,看到大家這個觀察,非常有趣。讀書會有第二段影片,他們對影片提出一些問題。但我也想請現場觀眾準備問題,雖然我們會看讀書會的問題,但就請導演挑選自己喜歡的回答,還是以線上互動的問題為主。
(播放影片〈Means of Ordinary Disruption〉)

讀書會成員1:我好奇的是怎麼重新建構脈絡?
讀書會成員5:我們討論的是演變過程嗎?還是資本家的目的?
讀書會成員6:我想要了解兩部片的後製,以及拍攝的過程?
讀書會成員7:這兩部片拍攝的方式介於虛構跟現實之間,是演員在建造那個空間嗎?通常我們在看一般紀錄片時,是把觀眾帶入真實的現場,但這兩部片卻是把觀眾帶入不同空間,讓我們看到好像是真正的故事。
讀書會成員2: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何謂真實?因為有官方文件記錄了過去發生的事,就是真實嗎?
讀書會成員4:我有一個問題想問《臨時工》的導演,片中有三個角色,木工、廚師與學徒,好奇角色是劇組事先安排,還是他們自己協調出來的?
讀書會成員3:觀眾都會想看到敘事的結局,但是很抱歉,這部片是沒有結局的,因為臨時工就是這樣,沒有開始、中間、結束。
林木材:看完了讀書會上的熱烈討論跟問題,不過我還是比較傾向線上觀眾,你可以舉手發言,也可以留言。剩下十分鐘左右,大家要把握時間。看起來,目前沒有(提問)。那我先請許慧如導演針對剛剛讀書會的問題綜合回答,或者挑一兩個想講的。
許慧如:我們一開始就設定好,找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年齡比較小,其他沒有多做設定,這是當我們在尋找臨時工時的基本設定條件。一開始也有嘗試讓他們去演出角色或扮演自己,但後來發現對他們來說,扮演這件事是有困難的。後來就是給他們工作,比如今天來漆這面牆壁,明天來釘這張桌子,快要過年了,來煮一頓飯吧。我們會大概給一些工作任務,但他們自己會去組合跟完成。非常有趣的是,某種程度上拷貝了他們在家庭中的角色,比如爸爸、媽媽、小孩。甚至在我們拍攝到中間,媽媽會跟小孩講,那你就把我當成你的媽媽來送禮物;爸爸會說,我一定要來這邊工作,不能去另外那邊工作,因為這邊不能沒有爸爸。當我們在現場聽到這些,也會被觸動到。自然而然地,他們把生命角色搬進來。剛剛有讀書會成員提到去脈絡化的問題,我會覺得這部片的結構、形式跟內容,之所以符合臨時工這一個命題是在於說,就像最一開始他們站在綠幕前,其實每一個臨時工被找來,沒有人在乎你的過去、家庭跟背景,他需要的只是一個勞動力,你今天來,幫我把十袋水泥搬上樓,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不管你是誰。只是説,今天當我們在這支影片內,重新組合起了「家」的關係。如果要講虛構,這個家大概就是一個虛構,在這裡組成,卻完全不存在,等他們這個臨時的工作一結束,就再回到各自的家庭裡去,這個看似幸福、溫暖、提供關係的家就會消散。如果要講虛構是這裡,但這個虛構,又讓我們看見某種程度的真實。
林木材:Joana跟Adirley,針對讀書會問題有什麼想補充?
Joana:不好意思我剛剛不在,我要回想一下剛剛講到什麼。讀書會提到幾個問題,有一位提到觀眾想看到敘事結局,還有虛構的故事裡面用了官方文件,好像跟現實有了直接連結。希望我特別回答哪一個?
林木材:我覺得可以選沒有結局這題,好像大家會期待看到清楚故事,但你們選擇不給結局。
Joana:其實我們在拍的時候,完全不知最後怎麼收。工作模式就是每天一直在反映這些人的生活,以及當時國家的政治、城市發生的情況。我們的確有劇本,但劇本只是募資用。拍的時候會有一些想法,但還不知怎麼實現,也不知結局怎樣,演員、導演全部人都一樣未知。幸好工作團隊的人數很少,可以很彈性調整,若是大團隊就比較難。也因為團隊小,有更多時間拍,這部片我們拍了十八個月。
另一個問題是官方文件。電影拍到一半,Léa入獄了。我們拿到那些官方文件(說明她為何入獄),還有Chitara那些很棒的獨白,拿到這些素材,就知道電影大概會結束在此,因為已經沒有出路了,已經太暴力太強烈了,這樣的收尾也非常有象徵性,因為這部片有簽署合約,證明有工作的演員竟然入獄了。我們也不想做一個簡單結局,官方文件中這些低畫質照片,就像虛構出來的一樣,也讓我們能繼續討論真實與虛構的問題。電影在最後,提供的不是結局,是一個混亂的狀態。Léa在這座城市成為一個傳奇,好像她的故事可以講給子孫聽。Andreia本來就住在瑟蘭迪亞,所以把她最後一個場景,做成好像是另一部片的開始,她跟摩托車騎士們正在騎車,好像電影沒有真正結束,還在持續下去,人還在流動中。
林木材:現在是台灣時間晚上九點,已經過一個小時,活動時間到了。最後想請Cíntia、Christopher或Jenny,有什麼話想跟導演或觀眾說?
Christopher:【藝歧連線】是一個開放社群,有興趣歡迎追蹤我們的網站,參與我們的下一個旅程。非常感謝三位導演參與。很高興建立這樣的交流,也感謝TIDF。
Cíntia:很高興能聽導演聊創作過程,我看你們的片真的是非常開心。希望大家能持續拍片,我們也能跟各位持續學習,感謝你們投入的時間、精力與情感。
Jenny:我把即將推出的活動報名連結貼在聊天視窗中。很高興參與今天的對話,看到這麼多語言的交流。我知道影展跟團隊都非常辛苦,很高興活動成功,謝謝大家。
林木材:非常謝謝線上參與的觀眾、導演跟策展人。很榮幸,TIDF作為活動一份子,也在影片、大家的談話,看見文化跟國際的多樣性,這是我覺得紀錄片很重要的一個特質。雖然「紀錄片」這個詞,本身也處在很多值得再被探討與再定義的狀態,但我覺得這幾位創作者都很勇敢去打破疆界,帶領我們看到更多世界樣貌。今天座談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